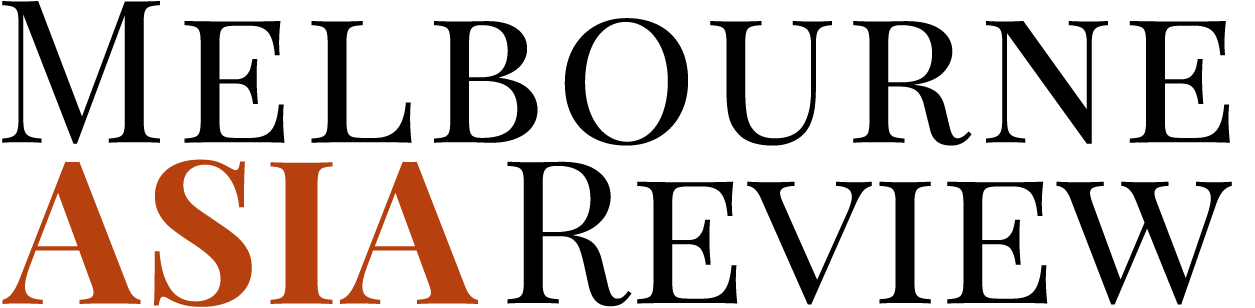慕容雪村是一位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他以直言不讳地捍卫言论自由和批评中国共产党而闻名。
在2020年4月,慕容雪村秘密前往新冠病毒最初爆发地武汉,在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采访了不同的人并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并以此写下他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 。
该书于2022年3月出版,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随着中国政府持续实施“清零”政策,本刊于7月25日采访了慕容雪村。
根据您2020年在武汉的采访和观察,请您讲一下当时在武汉的封控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带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我到达武汉是在2020年的4月6号,那个时候还有两天就解封了,武汉的控制已经不是很严格,有些人陆陆续续走上街头。在卖小吃的摊位前,在江边一些景点,已经可以看到走出家门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很少有人有笑容。
事实上武汉的封控远远比我看到的严重。在疫情最严重的二月份,武汉的封控政策十分严厉,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后来的上海【指2022年3月爆发的疫情以及随后的上海封城】,居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社区,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每个社区门口都有人把守。私家车辆不许通行,整个街上空荡荡的,跟一座死城一样。
请您用书中的一两个例子来展开讲一下封城对于个人的影响是怎样的?
比如说金凤【书中其中一个主人公】,她本来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清洁工,当时她跟她的丈夫先后都感染了新冠。因为社区封禁,他们不能自行就医,必须由社区先统计上报他们的名字。但是因为一个很小的错误——那个社区把他们的名字漏报了——所以他们就去不了医院。她丈夫的病情极为危急,吐血,极度的虚弱,但就是去不了医院。这个六十一岁的女人就跑到社区门口,跪在地上哭着喊着哀求社区的工作人员,把她丈夫送到医院去,但遇到的却是一连串的推诿甚至是斥责。后来社区终于派了一辆车,不过并没有将她病情危急的丈夫送进医院,而是送进了隔离站。然后,这个自己也身患重病的女人,用尽了她的一切心机、一切办法,给无数人打过电话,最后终于让她的丈夫住进了医院。不过为时已晚,没过多久,她就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你能看到处在类似境况之下的人,特别是这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危重患者,在这种极端严厉的社区封控之下,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有的时候就只能白白地等死。
再比如说,我的书里写的一位医生【书中另一位主人公】。他在隔离站做管床医生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患者发生药物过敏,喉咙肿痛、无法呼吸。医生看到这种状况后,就向隔离站的领导申请,说派辆车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那个医院非常近,开车过去大概就十分钟左右。当时也是情况危急,如果不及时送医,这个患者可能很快就会窒息而死。但隔离站的领导们,还有领导的领导们,没一个敢负责任,于是这位医生就不断地写 报告,手写还不行,还要用电脑打印出来,之后就开始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向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无数级的领导申请。申请到最后,领导们告诉这位医生说我们研究过了,要这么办:由医生来诊断病情,现场的领导们来决定如何处置。也就是说,之前所有申请都是白费,申请了一大圈,最后一切又回到原点。这个医生当时气得要死,在他的微博朋友圈里怒骂,说在我们医生眼里是人命关天,在你们政府眼里人就是个球。
那个患者比较幸运,她自己的免疫系统开始对抗这种过敏反应,所以咽喉的肿痛渐渐消退。如果不是这样,她大概就会死于过敏,死于极端的、毫无人性的政策。
那么您认为武汉封控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知道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也都采取了封控措施,武汉或者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不顾及人的生死。这是一个超级强大也超级高效的控制系统,却完全不在乎个体的生死与尊严。当张展【中国民权记者,2020年因在武汉追踪报道新冠被捕】在武汉采访的时候,她发现许多人的基本生活供应都跟不上,其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老人,她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网上购物,也没有亲人可以依赖,张展去给她送过两次菜,愤懑地想:要是没有我,要是只依靠社区,这位老人肯定就要饿死了。
在前段时间的上海,我们看到防控措施越发地变本加厉。我相信,在上海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独居老人,也一定有很多没有储蓄的年轻人,在这种极端罔顾人命的政策之下,他们一定会陷于饥饿,甚至会饿死。这样的事也许已经发生了。看看中国的感染病例数据,我想许多人都会有一种得不偿失的困惑之感,政府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这样呢?再想一想,你能发现,这种毫无人性的、过分严厉的防控,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它更多是为了控制社会、控制人。各级官员为了他们的政绩,层层加码,一层比一层残酷,却很少有人会想一想:这样残酷,这么惨重的损失,究竟是为了什么?值吗?
说到封城这个词,我们在中文里边叫“封城”,在英文里叫“lockdown”,它们是同一个词,但又有巨大的分别。大多数的西方人可能并不了解,在中国“封城”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封城,意味着你完全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意味着你的门上会被贴上封条,甚至会被钉死。它意味着你不能自行就医,不能外出购物,饥饿也只能忍着。它还意味着,那些你以为是自己的东西,可能并不真正的属于你。前段时间,在江西上饶,许多居民被赶出家门去隔离,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他们无权锁上自己的房门,因为政府要派人去“消杀”。同样的事情在上海也发生了,很可能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意味深长,或许可以引起那些沉浸在岁月静好之梦里的中产阶级的警惕,你以为你买的是十万一平米的豪宅,你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你的。但事实上,只要有个名目,政府就可以强迫你交出钥匙,就可以不经允许闯入你的家门。那么,你十万一平米的豪宅,还有你的存款、你的产业、你所拥有的一切,真的属于你吗?它们有什么保障吗?
接下来请您展开谈一下发表这本书对您来说的个人成本,以及其中的政治风险有哪些?
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写这么一本书意味着什么。整个过程也很惊悚。在我从北京去武汉的火车上,秘密警察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在武汉期间他们也不止一次地打来,以至于我常常会怀疑自己被跟踪,怀疑我住的房间里有窃听器。
后来我离开武汉也是因为一通电话。在我到达武汉一个月后,突然有一天接到了秘密警察的电话,他开口就问我:你去武汉干什么。我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我只是过来看看。然后他就说,啊看看,那好啊,你小心不要感染了哈,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这通电话听起来特别的平常,但仔细想想其中的意味,真是越想越害怕。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大概有100万字的采访材料。这通电话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告,我想我再待下去的话,有可能连这100多万字都保不住,所以我就赶紧离开了。
在后来写作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接到他们的电话,问我在干什么。这种时候总是很吓人,所以我一直都很在意安全保密工作。每写完一章我就通过加密软件发给我在海外的朋友,然后在我自己电脑上删除,写一章发一章,到最后一章发出时,真是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跟这位朋友说,你记下这句话: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这本书都要照常出版。
我当时能够想到,假如这本书出版,而我还在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仅是传唤、刑拘和坐牢,我还可能背上“汉奸” “卖国贼”这样的污名。
到去年八月份,这本书的出版社 Hardie Grant开始特别着急地催我离开中国,可能就是怕我会遭遇到这些厄运。他们一直催我,我就想,那好吧,我就试试看能不能走。其实什么都没准备。在8月7号的早上,我收拾了简单的一个箱子,带了两双鞋,两件外套,还有一些书,除此之外,我把47年来所积累、所建造的一切全都抛在身后,连我租住的公寓都没有退。一直到海关我都不确定能不能走得成。但是很神奇的是,海关居然没有阻拦我,我顺利地出关了。然后我才打电话告诉我的朋友,说我还租着公寓。我给他画了一个图,告诉他怎么过去,我的密码锁密码是多少,让他帮我把我的一些东西处理了。
后来这本书出版,Hardie Grant发了一个很长的通告,我也转发了。然后就来了许多水军,在下面谩骂诅咒,骂我是汉奸是卖国贼之类的。当然这个我也是习以为常了的。如果说到最大的政治风险和最大的不便,我想是这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可能没法回中国了。
对于当时秘密警察给您打电话我有一个疑惑,就是感觉他们采取了一种相对间接迂回的形式。我们知道您其实是位“老茶客”,也就是说一位被重点观察的高危人物。当他们知道您去到了武汉,采取的是查询和意味深长的警告,而不是直接干预,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当时我去武汉并不是特别公开的,秘密警察当然知道,但在公众层面,我并没有大张旗鼓。到武汉一周之后,我就绝口不提跟新冠有关的任何事情,在社交媒体上只发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比如我今天吃了碗热干面,在湖边看到了一朵花之类的,看着就像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所以他们可能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我去了哪儿、究竟在做什么,所以才会打电话来找我。
后来我在四川峨眉山里写这本书,他们又打电话来,我就说我在写一本科幻小说。然后跟朋友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故意在那讲这个科幻小说是什么故事、什么人物,如果他们真在监听的话,应该疑惑不定吧,觉得我可能真的在写一本科幻小说。我是这么想的,他们确实神通广大,但是他们不见得知道所有的事,我的这些措施有可能是有效的,他们可能会想,这个人确实去了一趟武汉,然后躲在峨眉山里边写东西。但我到底在写些什么,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确定。另外就是新冠的影响。其实从2019年底,也就是从新冠以来,我基本也“没喝过茶”。他们也害怕感染,也会尽量减少接触的机会。
不过现在的形势又不一样了。最近北京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前段时间收到一个邀请,某个大使馆邀请他去参加一个活动。对北京的异见人士来讲,这样的邀请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但他想了半天,最终也没敢去,因为国保很快就给他打电话,说某某老师,您要去大使馆,我们不会阻拦您,但是因为您跟外国人接触,有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您从大使馆出来之后,您的健康码有可能会变成黄色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健康码变成黄码这事有多么可怕,像我们这些人,被请去“喝茶”,甚至被拘留、被逮捕都是意料之中,很多人都做好了准备。但是健康码变黄甚至比这些更严重。因为你回不了家了,还会连累自己的家人,连累自己身边的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会被抓去隔离。所以这事甚至比坐牢更可怕。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你能想象到中国这种防疫政策,对我们这些人,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多大的影响。
接下来想请您再讲讲您这些年对于中共压迫言论自由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在您看来怎样的行为会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惩罚?他们又是如何恐吓和惩罚像您这样大胆发表个人言论的异见人士?
以前我认为我了解中国的审查规则,我以为我知道红线在哪里。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判断都在这个不断更新的大系统中失灵了,审查标准的越来越严格,底线越来越低,我已经不知道这个底线在什么地方了。
在2019年,新冠爆发前不久,有一天,大概晚上11点钟,突然两个警察就过来敲我的门,让我跟他们去派出所。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因为我在2016年,也就是3年前,转发的两条推特,两条政治卡通,都跟习近平有关系。他们就因为这个把我带到派出所去讯问,这在法律上叫“传唤”,要求我删除我的转推。那个账号是我以前用的,后来登录不上了,我就跟他们说我删不掉。后来他们又要求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再也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类似的言论。
据我所知,在那个时间段的中国,可能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的推特用户被警察传唤,被强迫删除了推特,并写下了类似的保证书。而且有的言论都不是新的,而是几年前的。
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我们几乎无法知道它的界线在什么地方,你看前几天那个“知了诗”
【指上海媒体人宣克炅在个人微博发出一首《致知了》的打油诗后被删文禁言事件】写的只是一只知了,完全看不出任何问题,也会被删除。
现在言论的尺度,可以说,几乎是无法让人说活了,写什么都有可能带来麻烦。最轻的是被屏蔽,其次是删除,然后会被注销帐号,接下来被警察传唤,再严厉还有可能坐牢。这五档五个层级的惩罚,随时都给你准备着。
罗昌平大概也不会想到,他因为一句电影评论,就会被判刑【指罗昌平因批评爱国电影《长津湖》被判入狱七个月并需公开道歉事件】。罗昌平是资深的记者,在中国言论场上 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士,但大概他也想不到能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到现在我们几乎无法判定中国的言论审查标准是什么样的,以及它会走向哪一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就是它接下来会越来越严厉。
下面我们来继续探讨中国持续的新冠相关管控措施。您的这本书讲述的是两年前武汉封控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这两年间的变化,接下来想请您展开讲讲中国这两年新冠管控的变化以及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清零政策。
我刚刚到武汉去的时候“健康码”还没有启用,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还不需要刷健康码,不然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到达武汉。但是就在我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期间,这个健康码就启用了。无论到哪里,坐出租车也好、你叫滴滴打车也好,都要扫码。到现在,这个健康码的控制系统已经变得非常的精细和复杂,不仅有各种颜色,还有带弹窗、带星号、带感叹号的种种形式。而且给一个人赋黄码或红码,也常常不需要什么依据,说你是黄码就是黄码。去年看了一个消息,当时还感觉震惊,现在已经渐渐麻木了。在黑龙江省的黑河,一座128万人口的城市,为了封控,政府一夜之间把全城128万人的健康码全部变成黄色,这意味着这128万人哪儿都去不了,寸步难行。
这样的政策现在已经让人感到非常的习以为常了。每次你感到惊悚的时候,它都能变得更加惊悚。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些封控措施,包括它的二维码统治、包括社区负责一切的制度,即使到了新冠病毒完全消失,它们也不会被废除。这些政策势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深远且长久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还比如现在的核酸。在很多城市,做PCR检测已经变成生活的必须内容,就好像充电一样,每个人过一段时间就得要去做一个检测,拿到结果以后才可以自由地出行。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它已经变得很荒谬,成为了一个比乔治·奥威尔笔下《1984》当中的大洋国还要离谱的国度。这就是这场灾难的作用。我认为共产党政府极大地利用了这场灾难,更加严厉地控制社会,大大地扩张了它的权力。我们可以说中国彻底地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所以您对中国政府新冠政策的感受是非常负面的。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社会里面的老百姓对于这两年封控的评价体会是怎样的?您觉得他们跟您持有相似的观点吗?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我们也时常能看见一些人持有相当正面的评价,比如说他们认为其他国家都不在乎人民的健康,只有中国政府最负责,类似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对于这两年政府新冠管控的评价和体会?
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所以我们很难知道民众的支持率是怎样的。但是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和见闻,我想大致可以说,因为信息的屏蔽和审查,可能多数中国人都相信国外的这种乱象是真的。
我前两天刚从美国回澳洲,这次旅行不需要提供 CovidPass,不需要提供PCR,一切都不需要了,像往常一样,只要拿着护照和签证就进来了。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生活已经逐渐恢复正常,所以也没有多少人会特别感觉恐惧。
但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在中国不一样。许多中国人都还很恐惧,我们可以想想这恐惧是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我认为政府的审查和控制系统有意地把这种恐惧传递给中国的平民。通过这样的庞大的系统,包括信息误导、信息控制、信息屏蔽,让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疫情仍然非常严重,而政府在保护我们。
此前您也提到像在上饶,居民要把自家钥匙都留给保安,还有上海封控中的种种事件都显示国家对个人强加的干预。您认为这些极端的防控措施是否有激发社会的不满?
我认为不满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看到,在上海,前些日子发布的《四月之声》和《六月之声》等视频作品,都被广泛传播。在武汉封城期间的《方方日记》也是这样。这种广泛传播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但还是得说,因为没有统计数据,我们很难说有多少人支持《四月之声》、《六月之声》,多少人支持方方,又有多少人在支持政府,但是我们能看到这种不满情绪的普遍存在。不过,这种不满在当下中国也很难持续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中国像是一个海底社会,海面上可能一切风平浪静,但在海底,在看不到光的黑暗之处,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那里生长,也不知道那里有多少漩涡或者暗流。
在这样一个社会,不满毫无疑问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种不满意会不会让中国政府改变它的这种过于残酷的防疫政策?我认为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向来并不真正重视民众的想法。
那么这种不满有没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制度性的改变?我认为至少近期也很难,基本上不太可能。但是这种不满就像种子,它们正在党国的探照灯照不到的地方悄悄滋长。或许有一天,它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改变。
This interview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was Darcy Moore.
Image credit: A worker performing COVID-19 PCR tests, Shenzhen, China, March 2022. Credit: Shengpengpeng Cai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