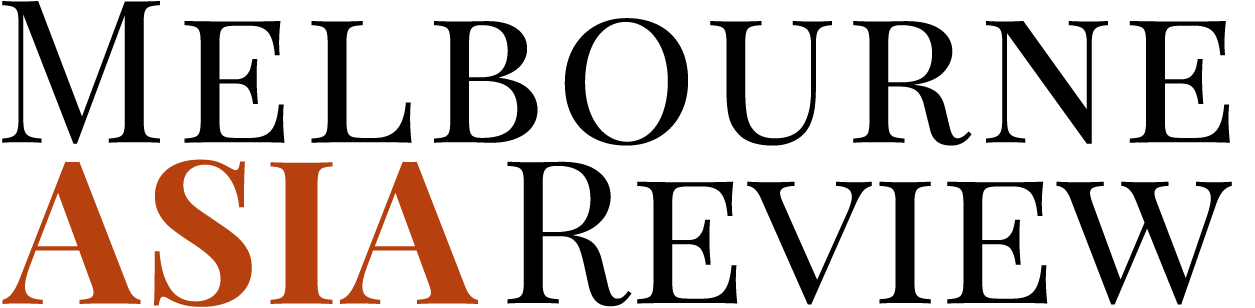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曹茗涵(Minghan Cao) , 杜旭臻(Xuzhen Du) , 李其霖(Qilin Li)
当今的印度尼西亚似乎仍然难以接受非传统的性认同、性别认同以及多元的性取向、性别取向。
2016年,印度尼西亚瓦希德基金会(Wahid Foundation)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只有26%的印度尼西亚人表示“不喜欢LGBT人群”。2020年,皮尤慈善基金会(Pew Foundation)的调查显示,只有9%的印度尼西亚人同意“应该接受同性恋”的声明。
温忠孝博士(Dr Dédé Oetomo)是一名活动家、印度尼西亚运营时间最久的同性恋人权组织GAYa NUSANTARA基金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艾尔朗加大学(Universitas Airlangga)有关性别与性的讲师。
《墨尔本亚洲评论》(Melbourne Asia Review)的总编辑凯西·哈珀(Cathy Harper)对他进行了采访。
您会如何形容印度尼西亚LGBTIQ+群体的法律和社会层面的处境?
很糟糕。打个比方,在情人节时,很多小城镇,或是没那么小的城镇里,所谓的治安警察,有时是正规警察,他们不会去搜查万豪或者凯悦那种大酒店,只会挨个突击搜查便宜的小旅馆,重点搜查其中可能有男人或女人独住的房间,或者两个男人登记入住的房间,因为他们可能是男同性恋。事实上他们无权进行搜查。有些地方政府的法令甚至有关于计划开设包括性取向转换疗法在内的康复中心,并且他们还自认为这是在通过改变男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者来帮助他们。这种心态是完全不对的。一些政府的部门将之当作获得保守党支持者们手中选票的手段,甚至在非大选期间也是如此。八月时,我的组织与一位同性恋活动家共同举办过一次庆祝独立日的活动。活动地点附近的居民们和村长以及警察们一起过来,打断我们的活动,说“这绝对不行”。这确实是发生在独立日的事情,简直就像荷兰警察在独立前夕破坏了一场民族主义者的会议一样讽刺。
您认为保守派伊斯兰政党会在二月的大选之前大肆利用LGBTIQ+群体的话题来获得选票吗?
相比于2014年,2019年时他们已经相对收敛了。事实上,2016年才是有关同性恋恐惧、跨性别恐惧的仇恨演讲最多的一年。大多数部长、议会成员都是保守派,他们必须作出声明。有趣的是,宗教部的部长声称LGBTIQ+群体的权利不可侵犯,因为他们同样也是印度尼西亚公民,但他却说我们需要将他们带到“正途”上。接着他就被伊斯兰媒体打上了“同性恋部长”的标签。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在一些地区,比如亚齐省和西爪哇岛,保守派的优势更大,但在像雅加达和日惹这样的城市里也同样糟糕。
举办各种公开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有关跨性别女性的活动,尽管举办这种露天活动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已经是传统了。甚至在90年代,泗水市每周四晚上都会在一座游乐园里举办变装秀,几乎每个人都会参加。报纸上会进行宣传,在游乐园外也会挂大型条幅。我曾经带澳大利亚的艾滋病顾问去玩过,并且说“这是每周一次的马蒂格拉斯狂欢节 (Mardi Gras)!”。更大的群体会来参加变装秀,并且玩得很开心。但现在这些都不可能了。在巴厘岛有个同性恋区(但别这么叫它,不过确实有这个地方),我怀疑是交过保护费的。就算是在巴厘岛,有些活动也被迫取消过。尽管上次骄傲月的庆祝活动被允许进行——每年六月全球性少数群体会举行一系列游行庆典活动——但那是在巴厘岛,并且没人能保证下次还能举办。这就是现状:无法公开。哪怕你举办的是培训工作坊,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会有保守派注意到你,并且只要他们看到了跨性别女性或性别表现不一致者,他们都会向警察举报。令人非常害怕的是一些私人活动也会被突击检查。那活动有可能只是一帮男人去谁的家里玩。这是发生在雅加达市区的真实事件,一所中产阶级的房子,被警察带着举报者搜查了。这些举报的人想成为社会道德的守护者。偶尔也会有人被告知需要离开居住社区。一对情侣在雅加达的上层中产阶级社区租房时,被社区主席打电话告知“你们不可以住在这里。我们知道你们是同性恋”。这对情侣本可以在法庭上质疑,但考虑到之后有可能被媒体报道,所以他们决定搬走,没有起诉。
很多家长知道或者怀疑他们的孩子可能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跨性别者或者是非二元性别者,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就会请牧师,或者请萨满或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来为孩子“驱魔”,抑或是采取转化疗法。这很吓人。有些时候,由于亲戚或是父母可能有暴力倾向,跨性别的孩子们不得不离家出走。有关暴力层面的研究寥寥无几。据我所知,唯一的相关研究是由亚太跨性别网络进行的,但这种研究很难被量化。我们尝试过在多个组织训练活动家,让他们监测并报告暴力事件。这很困难,而且我们根本收集不到数据。
那么在印度尼西亚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情况如何呢?
在男同性恋群体中,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仍在上升。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是分开统计的。因为在巴布亚省,艾滋病是流行病,我认为这里的感染率约有2.5%,这个比例相当高了。统计数据的难点在于,很少有男同性恋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艾滋病感染率仍在上升。我不是流行病学家,但在我看来,感染率在明年年底可能开始趋平。我依旧会听到关于男同性恋死于艾滋病的消息。有趣的是,跨性别女性群体的感染率已趋于平稳。我觉得这是因为如果你是跨性别者,无论如何你的特征很明显,是无法假装自己是所谓的“正常人”。对于男同性恋来说,公开性取向是很可怕的。因为即使在一些医疗中心,有些医护人员可能有同性恋恐惧症。而且如果去诊所看病的话,父母或兄弟姐妹可能就会知道他们的身份。所以,我们觉得就算制作了艾滋病毒信息宣传手册,反正也会被扔进垃圾桶,不如不做。但幸运的是,有些人很勇敢,愿意去政府医疗中心接受志愿检测,这些检测大多是免费的。如果你和同性恋组织或LGBTQ+组织有联系的话,你会更有保障。即使你已测出艾滋病毒阳性,你仍可以拿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卫生部也在尝试使用暴露前预防药物(PrEP)。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条件优越者或者处于上层中产阶级的人群,通常会去巴厘岛和雅加达的私人诊所接受治疗。超级富豪们则会去曼谷拿三个月的ARV或进行检测。疫情期间,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且实际上许多艾滋病毒相关的服务都取消了,因为护士们都在忙着给人们接种新冠疫苗。但现在新冠疫情结束,事情都在回归正轨。
同性婚姻在印度尼西亚会被允许吗?
乐观来看,我会说是有可能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如果你想要印度尼西亚独立,人们会觉得你疯了。荷兰情报警察会骚扰你,还可能会流放你之类的。在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独立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经历了危机,二战和日本侵占后,印度尼西亚独立了。尽管不完美,但我们独立了。所以我会说,在一些前提条件的加持下,同性婚姻是有可能实现的。
印度尼西亚是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前几天,印尼总统非常骄傲地说“我们国家93%的人口都相信上帝”。但我们国家的官员涉及腐败或因腐败入狱的比例呢?更重要的是,在有信仰的群体,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有人正努力发展更人性化,更进步的信教方式。如果这些人成功了,我是说“如果”,那在未来的三十或四十年后,我们就能见到一个更人性化的印度尼西亚。这是一种可能。指望国家上层的政治家们是不可能的,但在东印尼,有像特纳特、安汶、库潘和毛美雷这样的一些小城镇,至少是在讨论一些本地条例来保护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我看了一下安汶的条例内容,其中并没有提到LGBTIQ群体或性别问题,但库潘的条例中可能包含了相关内容。2020年,一个保守派伊斯兰政党在国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所谓的家族韧性的法案。意思就是作为家长,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是跨性别者或有此倾向,但没向当局报告,你就会入狱。这项法案并没通过。
我认为实际上我们的人权活动,在亚太地区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在国家层面上,他们讨论了一项保护在性取向和性别上的弱势群体的法案。必须督促国家,必须抗议。最后,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教导年轻一代多点包容和接纳。比如,澳大利亚在1978年的第一次马蒂格拉斯狂欢节,仍有超过五十人被逮捕,且他们的名字被公开列在《悉尼晨锋报》上。但45年后,马蒂格拉斯狂欢节仍在举办且非常安全。尼泊尔最高法院的法令已允许同性婚姻,尽管有些地方婚姻登记办公室拒绝遵守该法令。下一个可能就是泰国,我们希望前进党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在印度尼西亚,我们的阻力是宗教,泰国的阻力是军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普通年轻人的朋友圈或家庭中,您是否看到了更多的包容性?
是的,特别是在我课堂上的学生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更多包容性。不过,我的课程是选修课,学生是自愿报名的。但有些年轻人会到我家,羞涩地讨论性别和性取向问题,后来他们承认自己都是酷儿,所以这类人群确实存在。当然,其他类型的人也存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印尼语频道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上的相关评论中,常能看到一些非常可怕、充满仇恨的言论。不过,这些言论并不是独创的,只是无知的表现。我希望通过教育,能够减少这些仇恨言论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在学校性教育以及性取向和性别教育方面的总体情况如何?
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只会有一些“生活技能”教育。如果不巧的话,你的老师可能会说“等你们结婚,成了成年人,有了孩子再说吧”。社会上有抵制情绪,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生孩子和不结婚。我认识一对未婚异性恋情侣,他们在租房时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担心由于未婚同居行为(印尼法令禁止未婚同居)被举报或赶出去。幸运的是,现在有了互联网,各种信息都可以找到。在我那个年纪,获取信息非常困难。至少在苏拉巴亚,一些高中了解我的组织,有些学校甚至会邀请我们的活动家去演讲。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公开做这件事,只能秘密进行地下活动,我们称之为“游击战”。
您能谈谈您认为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制度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不同性取向和性别的人群的事业吗?
民主确实有帮助,尽管它并不完美,而且明年的全国大选形势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的组织被政府关闭,我们可以求助于主流人权捍卫者盟友,他们会为我们抗议,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您认为伊斯兰教接受同性关系,您的依据是什么?
这种说法很有争议。但确实有一些穆斯林酷儿活动家对伊斯兰教经文进行了新的解读,还有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学者安·安肖里(Aan Anshori),他是我们的盟友,他的论文研究了在伊斯兰教法下同性婚姻的可能性。他的观点是同性婚姻基于爱,而爱是真主的恩赐,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谴责爱呢?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它确实存在,而且不断发展。自 21 世纪初以来,我就看到这种趋势在增长。
在伊斯兰教法中,实际上提到了双性人。真主创造了男性、女性和双性人。在先知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位跨性别女性,我们甚至知道她的名字。安肖里还告诉我另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男人来到先知面前说“我喜欢那个男人,他很英俊”,先知说“这个人喜欢你!”。这些例子确实存在,但人们喜欢在宗教中断章取义。关于《圣经》,人们觉得它很难解释,他们只想要一些简单的答案。我那些宗教界的同仁既人道又进步,他们正在努力启发人们思考。显然,至少对穆斯林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责任,你必须运用你的理性,你必须思考你的宗教信仰。
您如何看待人权语言?你认为这是改善LGBTIQ+群体状况的有效途径吗?
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尤其是穆斯林,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不仅是穆斯林,许多华裔也倾向于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西方很糟糕。当然,对我来说,我更愿意站在西方一边,因为在那里,我的同性恋权利能得到保障。我无法想象生活在中国的情景,他们已经开始封锁LGBTIQ+群体和其他所谓“有问题”人群的社媒账号。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喜欢俄罗斯,他们渴望强有力的领导者,并认为民主制度混乱不堪。我们只能通过教育改变这种情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您一直是印尼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家之一,我想知道您认为目前印尼的LGBTIQ+活动的影响力和运作如何?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影响力相当强大。我们不像菲律宾,他们的LGBTIQ+运动比我们更强大。但当我和来自缅甸、中国的朋友交流时,他们都很羡慕我们。他们羡慕我们能够存在,羡慕我们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及我们的工作,并谈论人权和性别问题。据我所知,只有两个LGBTIQ+组织在他们的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到这个词。至于其他组织,法务部官员让我们称自己为“帮助人类的社会组织”,甚至连“人权”或“性别”这样的词汇都不能使用。其实很简单:虽然听起来有些陈词滥调,但如果你遵从自己的内心,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是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尽管有很多压迫,你也会努力地生存下去。我们可以在亚齐的跨性别女性(在印尼的亚齐省,跨性别女性甚至会被拘留并教育要“像个男人”)中看到这一点。她们依然存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有三到五个组织,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一百多个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图片来源;Ikhlasul Amal/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