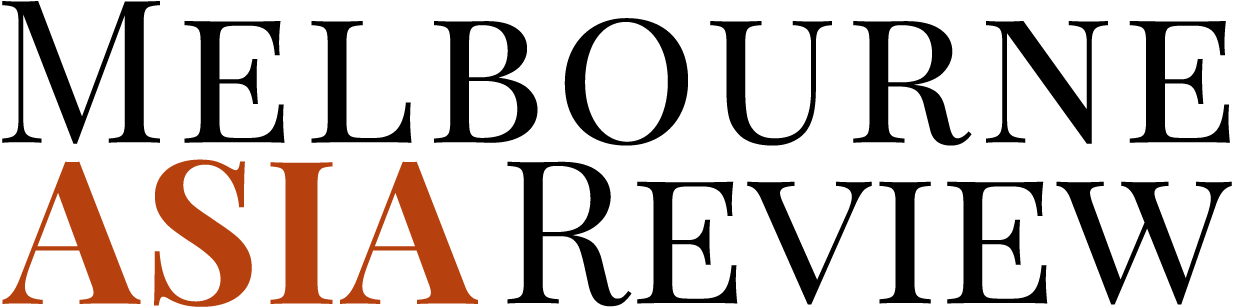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郭慧喆,乔书华(Joshua Peace),林军杰,武嘉翼
毫不夸张地说,澳大利亚与日本双边关系是澳大利亚二战后外交中一个极为成功的案例。首先,在与澳大利亚建立双边关系的亚洲国家中,日本称得上是最重要并与澳大利亚建交最久的国家。总的来说,澳日双边关系可以概括为一种亲密、稳定且高收益的关系。因此,日本对澳大利亚整体政策的制定有深远影响。最初,澳日两国关系以1957年签署《商业协定》后的大规模贸易为基础,后来,两国间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多层面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即保留了广泛的商业联系,又愈发重视安全与区域合作。
此外,澳大利亚与日本两国的国家安全都仰赖美国,并且两国都强烈支持自由贸易、法治、民主与人权。这些共同点让日本与澳大利亚在过去五十年里在不同领域中有密切协作。这些领域包括非传统安全与经济安全问题,又可以细分为自由贸易协定、援助与发展项目、对抗气候变化以及海盗行为等。
即使因为捕鲸问题以及2016年澳大利亚因处理不当导致“潜艇交易”由法国投标方应得而非日本、使得澳日两国关系变得紧张,但近年来澳日两国关系持续升温。双边关系升温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澳日两国共同关注的中国称其拥有中国南海争议岛屿主权事件,二是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以下简称为印太地区)对美国的直接挑战。尽管如此,澳日两国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不难理解,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的政治僵局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占据了澳大利亚国际政治头条,因此分散了对澳日关系发展重要性的报道。
澳日关系的持久性以及政府和次国家层面的关系进展都表明,在许多方面没有出现此类报道并不令人惊讶。在过去的60年间,外部因素与两国国内的首要任务导致了其双边关系管理中的“高潮”与“不作为时期”,以及一种自满倾向。然而,两国对于美国保持其在印太地区平衡中国的重要地位的共同期望,使得澳日关系近年来取得巨大进展,并且让此双边关系在拥有共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达到新高潮。
牢固的安全关系
澳大利亚与日本在政治安全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起点较低,但在中国逐渐成为印太地区现状的影响因素前,双方的协商和合作已经顺利展开。特设安全协商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步增加协商次数。截至20世纪90年代,澳日双方互派防务专员,澳大利亚还支持日本参与联合国在柬埔寨(1992-93)与东帝汶(2002)的维和行动。然而,加速推进两国已经稳健发展的政治或安全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美国的“恐怖袭击”(911事件)。在许多方面,安全协商是基于贸易互补性与密切政治关系的紧密双边关系中所缺少的一环。随后,一系列的双边交往、备忘录与协定将2007年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推向高潮。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是二战后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日本签署安全协议的国家。此安全协议虽然为两国发展安全关系,如年度部长级协商(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间的“2+2会谈”)与稳固军事关系等活动提供了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协议。例如,两国间没有规定在一方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为对方提供军事支持。相反,此宣言的重点是非传统安全,如处理难民危机、环境灾害与人道主义和发展问题。由于《日本宪法》的第九条限制了日本自卫队的作用,这一宣言不仅适用于两个国家,对日本来说也是必要的。
与之相关的是澳、日、美三国三边交往的发展,即“三边安全对话”(TSD)。2001年7月,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首次提出这一观念,以此打击印太地区的恐怖主义,同时巩固现有的安全关系。自2002年以来三边安全对话年度会谈的发展使美、澳、日三国密切合作,并通过联合训练与共享情报信息确保军队之间互用性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一进程提高了这三个国家军事与情报体系的效率。
自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以来的15年间,定期的安全升级确保澳大利亚与日本两国开展密切合作、经常性会议与军事训练(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本土的军事训练)。2020年11月,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关系提升为“特别战略伙伴关系”。正如特别战略伙伴关系所言,澳日两国的密切合作、经常性会议与军事训练(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本土的军事训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正如托马斯·威尔金(Thomas Wilkins)指出,通过“特别战略伙伴关系”机制进行的双边合作已逐渐巩固,并成为澳大利亚与日本间外交、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常态”。经过几年的协商,澳日两国于2022年1月6日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RAA)加固两国间的关系。这项历史性的协定使澳大利亚和日本两国军人能够不间断地进行联合军事行动与作战演习。这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此类协议。
中国引起担忧
毫无疑问,近年来澳日两国安全措施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两国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直接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担忧。如今,作为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中国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确立了自己作为美国对手的地位。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强硬立场,以及中印士兵在边境上的冲突,促使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以制衡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和影响力。
对澳大利亚和日本而言,这意味着要加倍努力与美国协调,伸张其在中国南海的通行权并推动“自由开放印太”(FOIP)框架。此外,在现有双边安全网络的基础上增加了安全合作,丰富了双边关系,并扩大了双边和多边安全倡议。将印度纳入原来的三方安全对话(TSD),形成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是最典型的例子。“四方安全对话”成立于2007年,但在2008年解散,主要因为不想冒犯中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回应了中国的崛起并成为了美国的直接竞争对手,而且正如最近在墨尔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表明,对话的重启也回应了各方对一些地区既定秩序瓦解的担忧。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和日本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澳大利亚不断恶化的对华关系不同,日本自2014年以来与中国的政治关系逐渐缓和,外交关系逐步改善。尽管太平洋战争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钓鱼岛(也称“尖阁列岛”)的领土争端持续,以及日本与华盛顿的关系日益密切,但中日关系依然实现逐步缓和。
日本所作出的重要举措是其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的其中一步,这种努力已经改善了中日两国间不融洽的关系。如今,两国的交往非常务实,而且日方注重与中国领导人的沟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新冠疫情带来限制,且日本对“四方安全对话”和“自由开放印太”框架表示支持,部长级的高级别面对面会谈中仍让中日两国达成共识。这个协定维护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并通过与韩国的三方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来实现。如果该协定全面实施,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日本采取与中国的“互动政策”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个政策很务实,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上一财政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占日本总出口的22.9%。
尽管如此,在过去几年中,日本愈发关注中国对持续的领土争端所采取的侵略性立场以及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发生“热战”引起了日本高级官员担忧。考虑到台湾靠近日本领土,而且,倘若要通过军事途径保卫台湾,美军会使用冲绳的基地,从而将日本卷入冲突,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2021年7月麻生太郎副首相在国会作证时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将威胁到日本的生存。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制定了一个在两种模式中切换的政策。模式之一是注重商业关系与经济合作温和政策,另一个是与中国交涉时保持强硬政策。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和他任期短暂的前任菅义伟(Yoshihide Suga)一样,一直坚持这一做法,并在内阁中保留了对华强硬派,包括国防部长岸信夫(Nobuo Kishi,安倍的弟弟)。岸田在2021年11月初仅失去12个席位的情况下取得选举胜利,这意味着自民党和公明党联盟在国会中保留了绝大多数的席位,因此,纵使在中国对有争议的中国东海事件中表明强硬立场的情况下,岸田政府也获得了权力推动提高国防开支(包括将国防预算翻倍至GDP的2%),以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立场。属于自民党内部亲华派系的岸田将这些政策带入选举中,并且在国会中取得相对的成功,反映出日本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态度更显强硬的决心。
2022年澳日双边关系热点聚焦
1.通过四方安全对话促进地区和平
在发展更加强大的军事关系以外,第二次四方安全对话还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发挥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优势。关键合作案例包括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以及针对印太地区问题开展关键技术合作。这些政策为两国奠定了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发展基调,与两国区域外交相得益彰。考虑到各国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澳日一直小心翼翼,避免与中国对立或激化本就紧张的安全关系。疫苗外交显然是疫情期间的优先事项,“四方”国家虽然在疫苗供应方面与中国存在竞争,但仍占据优势。此外,气候变化也是一个不错的议题,中国在其中扮演合作者而非竞争者的角色。这三项倡议结合起来,旨在构建一个对中国具有包容性的环境,这可能说服其他国家打消对四国安全对话的疑虑。
2. 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对中国采取包容性态度的又一次机会。CPTPP设立之初是以自由贸易体的形式来抗衡中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人们担心中国的加入可能会改变该组织的体系和政策方向。目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正在审查该申请。 两国均希望中国能够遵守CPTPP协定中包括关于透明度、关于不歧视国内外公司等多项条款。澳大利亚官员也坚持认为,中国需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贸易禁令,并恢复部长级对话。澳日双边关系中的矛盾的潜在来源是日本可能会支持中国的加入,而澳大利亚则并无可能这样做。随着日本采取与中国经济往来的政策,澳大利亚与北京的关系却急剧下滑,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越南与中国具有相似的经济特点,却能够通过特殊条款成为其中一员,这也提高了中国加入CPTPP的可行性。理想情况下,东京和堪培拉统一战线,推动中国的加入协定。这说明澳大利亚对中国采取的新政策,需要给予更巧妙的处理,使其既能接受争端又能实现合作。此类政策满足了澳日两国希望中国成为区域一员的愿望,成为其增加沟通和规范制定渠道的战略组成。
3.日本与澳英美联盟
虽然此前表示与中国修复关系已取得一定进展,澳英美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UKUS)秘密建立并于2021年9月高调宣告成立,澳英美联盟的成立是对抗中国在地区事物的影响力上的又一层安全对话。截至目前,三方初次会议主要事项为澳大利亚取消与法国潜艇公司的交易合同,转而与英美开展核潜艇技术合作。意料之中的是,日本已正式承认AUKUS,因为该协议重申了美国对日本的承诺,并为日本带来英国和澳大利亚两个积极的合作伙伴。不过,考虑到法国潜艇合同以如此粗暴和无耻的方式终止,日本官员无疑会对本国于2016年潜艇招标的失利而感到欣慰。
东南亚国家对AUKUS的反应不尽相同,它们担心此举将东南亚诸国排除在地区进程之外,甚至会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如果日本通过利用外交手段以及联系精英人士来吸引各国加入,那么日本的支持对AUKUS来说将是一个重大贡献。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和四国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加上其与该地区国家的紧密联系,人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会成为连接AUKUS和东南亚之间的桥梁。具体来说,建议日本外交官可以协助与东南亚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制度化的沟通和对话。
不过,日本官员可能不愿为AUKUS在东南亚做得太多。东京国防安全早期评论的重点在于AUKUS是如何强调英美间的联盟以及给日本造成一种被排斥的感觉。鉴于日本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间存在密切的安全关系,并且与英国又保有相对稳固、长期的双边国防关系,未来日本将有可能加入AUKUS。但是,向第三方泄漏信息一直是日本政府和官僚圈的顽疾,这将是日本加入AUKUS的一个潜在的障碍,也是过去日本希望加入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组织时的一大阻碍。
4. 新方向:气候变化和零排放合作
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零排放目标方面的战略合作,为澳日伙伴关系指明了新方向。日方承诺,截至2030年减排46%,这既是其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一部分,也是澳大利亚开发清洁氢能以减少对燃煤电厂的依赖并作为出口商品的举措的补充。尽管双方都不是气候变化行动的领导国,但两国领导人于2020年1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寻求清洁氢能机会,目标是截至2030年向日本出口一百万吨清洁氢能。此项举措令人鼓舞,能够向两国政府施压,让双方均在此方面作出更多实质努力。目前预测,到2050年,氢能出口可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价值高达260亿澳元。这反映出澳大利亚从消耗煤炭过渡至消耗清洁能源的潜力,对双向贸易以及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月,澳大利亚和日本扩大了清洁氢能计划的合作内容,提出使用财政激励措施,鼓励该地区其他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行创新。
总结
过去15年中,澳日关系在政治安全领域取得了非凡的进展。澳日军事界现在通过定期的双边、三边(与美国)和四方(与美国和印度)对话彼此熟悉。此外,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确保澳大利亚和日本军队之间的协同水平和作战能力将不断提高到上一辈人无法想象的规模。
重要的是,安全合作的迅速推进表明,澳日间伙伴关系是两国在制定各自安全和外交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选择澳大利亚作为除美国以外的第一个签署安全合作协议(2007年)和互惠准入协定(2021年)的国家,这一事实象征着双边关系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事实上,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现在已近乎与两国之间的巨大商业联系相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但它成功地与中国保持了外交对话和大规模贸易关系。日本这一处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的模式并不完全适合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要与中国重新进行良好外交,日本这一模式是值得借鉴的:虽然中国和澳大利亚依然会有强烈的分歧,但在有共同利益的关键地区问题上存在外交沟通、贸易和合作。
最后,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双方享有共同利益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气候变化和零排放政策方面的合作就是明证。这是一种自然的伙伴关系,其基础是能够经受住困难时期的互补性和共同利益。这些共同点表明,澳日双边关系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繁荣发展。
Image: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and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Hayashi, Melbourne, 2022. Credit: US Department of State/Flickr. This image has been crop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