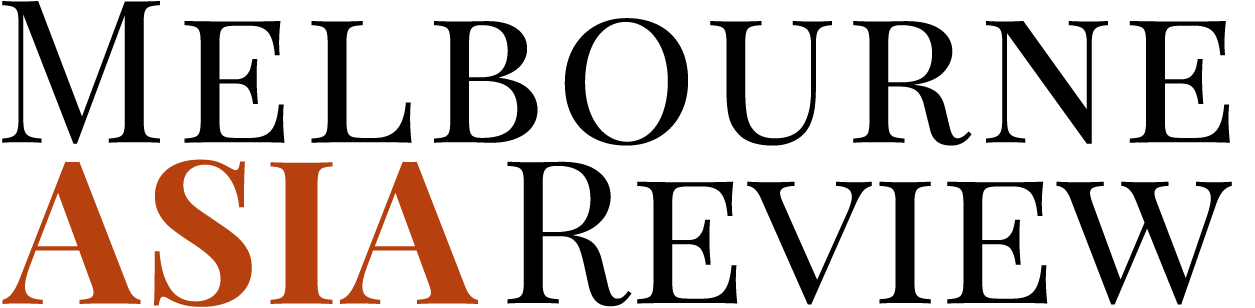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王淳(Chun Wang),徐冰(Bing Xu) ,王宇宁(Yuning Wang)
新兴援助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正在改变国际援助的局面。随着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中提供了另一种发展合作方式,受援国内便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及经济竞争。长期以来,这一领域一直由英国、美国、欧盟及澳大利亚等援助方主导。
在缅甸和柬埔寨等国,驻扎着一些新兴的西方援助机构,他们对该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定位备受关注,相比之下援助领域内“人权”等关键词的含义及其用法之争却鲜有人了解。随着中国援助影响力的提升,有关“人权”一词的争论是如何在国际援助领域内展开的?各援助国是如何力图说服亚洲受援国的各行动方,内化符合其偏好的人权含义的?
本文所探讨的新争论介于中国政府和西方援助国之间,前者在援助领域内强调“发展权”概念(right to development),后者担忧这会转移对个人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关注。笔者认为,研究中国援助的兴起及其对全球援助架构的影响力时,除了地缘政治及经济定位外,还必须关注“人权”等词的含义及用法上新出现的重要争论。
中国援助影响力的上升
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援助并非总是以连贯集中的方式进行协调的,而是在实施时会考虑到政府各部门、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的多方利益。笔者在此提及中国援助和利益时,并不希望淡化多方利益的博弈。
在分析中国的发展合作方式时,学者要么批判中国所谓的利己主义动机(包括指控中国是“帝国主义者”或者中国在施行“流氓援助”),要么关注中国对这一指控的回应上。不管研究的强调点在于将中国援助正当化还是丧失正当性上,都意味着在更广泛的国际斗争开展时,受援国通常仅被刻画为其中的背景板,因而淡化了中国援助所带来的多样影响。
同样要注意的是,以具体可行的方式比较中国及西方各国的援助颇具挑战性。“对外援助”及“发展援助”(ODA)在定义上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更为广义,后者则是更狭义的国际定义,包括各类贷款和拨款的比例等标准。由于中国广泛开展优惠贷款及其它资助,中国援助提供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并不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定义的发展援助类别。
然而无论衡量标准是什么,中国政府的国际援助资金拨款在过去十年内显著增长,从2010到2012年间的平均40亿美元每年,增至2019年的近乎60亿美元,高于澳大利亚国际发展援助资金额。除了援助资金额的增长,最近两个关键变化进一步凸显了在国际援助论坛中话语权斗争的重要性。
首先,中国于2018年设立了新的独立援助机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及外交部争夺决策权,援助项目零碎分化,而CIDCA减少了这种分化,且获得的授权更广泛,能够代表中国政府商定并签署国际协议。
有趣的是,新独立援助机构的创立与过去十年来传统成员国内的趋势相反。OECD各成员国都越发关注国家政治与贸易利益,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都将其部分援助机构并入外交部和贸易部。相反,中国新的独立援助机构以及增长的援助预算表明其在发展合作领域的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与很多传统援助机构不同,CIDCA的既定目标并未明确包含促进人权,却也并不回避使用人权话语。CIDCA定期会在其官网上发布来自中国高层官员的讲话及外交访问的文稿,而对人权的讨论一直是其核心所在,文中涉及“人权”的内容各不相同。
一方面,CIDCA试图将中国树立为全球人权行动方。比如在2022年2月,CIDCA官方网站重新发布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有关“坚持公平正义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讲话。
另一方面,CIDCA对使用人权语言正当化外国干涉的行为提出警告。比如该机构曾发布王毅于2021年8月进行的讲话,他当时警告某些国家,称其“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试图追求自私的地缘政治利益”。作为新的独立机构,CIDCA展现出中国政府在参与全球发展辩论,及支持其“人权”方面的话语上日益增强的信心。
其次,2021年,中国政府新发布了一部援助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这是其中的第三部,也是其最为雄心勃勃的白皮书。与2011及2014年的两部相比,新白皮书在措辞上有关键改动,强调的是南南合作而非“对外”援助。
重要的是,新白皮书还直接将援助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联系了起来,更加强调“人文资源”,这包括受援国的政策及治理能力。
最后,白皮书还强调中国在主流发展话语中的参与度,其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中国对联合国做出的贡献。因此,虽然白皮书并未明确涉及促进人权,但却将中国置于主流发展对话之中。
在过去至少十年间,中国在塑造国际发展合作,包括在联合国及其他援助论坛中参与治理、问责和权利相关的话语中所起到的作用日益增强。然而综合来看,这个新设立且资源充裕的独立援助机构及白皮书表明中国将在未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曾在2018年充满信心地宣布中国应“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然而,越发深入地参与国际发展论坛虽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机遇,但令其陷入了窘境。一方面,联合国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用以“提升形象”的平台,近年来中国“影响联合国规范性架构的潜力”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中国本国的人权记录及其在国际援助及投资中的人权记录受到更多国际方面的审查。
因此,随着中国活跃在联合国各论坛及国际性的发展合作之中,他们不得不重新诠释和调整人权的含义,以支持本国的发展政策方式。更广泛地来说,中非关系专家琳娜·贝纳布达拉(Lina Benabdallah)将中国政府的策略描述为“支持国际秩序,或同国际秩序融合的同时,也会对其中不符合本国偏好的部分秩序进行改动”,包括人权的某些特定含义,比如那些基于个人自由的含义。
中国参与国际发展论坛的力度加大对于国际援助的未来意义重大,为西方主导的援助范式带来了一种“深层危机”。这一危机不仅关乎西方各援助国对受援国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影响减弱,还涉及中国的参与给围绕援助及发展合作的全球话语所带来的挑战,而这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援助国所主导。
全球援助架构中围绕民主、问责和人权含义的核心共识正以新的方式受到挑战。因此要想理解国际援助领域内的变化,分析日益增长的人权含义的话语争论就愈发重要。
对人权含义的话语斗争
在探讨新出现的人权含义争论前,这里要注意,笔者在此主要关注的人权是作为话语,而非作为一套国际法律文件及原则而存在。
过去十年间的研究,尤其是在人类学学科中的研究,揭示了人权话语在不同语境间如何转变,及其作为含义存在时,各政治行动方又如何利用人权话语实现特定的目的。人类学家萨利·安格尔·梅丽(Sally Engle Merry)描述了“话语本土化”(vernacularisation)的过程,即地方行动方对人权的全球含义作出调整适应本土,从而创造出混合含义的过程,含义中结合了全球参照含义与地方文化特色的两方元素。
在审视地方语境中的人权话语斗争时,“话语本土化”的概念很重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概念基于一种假设,即人权的“全球”含义是稳定不变的。随着中国在国际人权论坛,尤其是联合国中的参与度日益加大,且愈发坚定自信,挑战了先前西方成员国间对于“人权”一词达成的广泛共识,这种假设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转变。
当然,对于规划受援国项目时应相对更看重哪类权利的问题,各援助国间长久以来一直争执不下,因此笔者并不希望将中国以外的援助国刻画成一副彼此完全一致的模样。但在近几十年来,西方援助国国际援助项目的核心一直都是民主、人权、治理得当及问责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含义及规范价值方面具有广泛的共识。
相反,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援助项目强调了对主权的尊重、无附加条件的援助以及促进自力更生。因此,对于中西方援助项目在受援国发挥的作用,以及关键概念的应用方式方面,存在着诸多争论点。
在国际援助论坛中,尤其是人权这一概念,一直以来便是中国和其它援助国间的争论点。中国及人权专家傅若诗(Rosemary Foot)对中国在联合国有关人类安全方面的参与进行了分析,分析中认为联合国历来重视发展、人权及和平与安全间的联系,而中国政府正在挑战这一传统,其“三元模型”反而强调经济发展、国家强大及社会稳定。因此,中国政府正试图淡化安全方面的个人人权重要性。
然而,不仅是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其定义也受到了威胁。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人权的含义向“发展权”的方向转变,各方共同强调较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而非个人公民及政治权利。人权专家邦尼·伊巴瓦(Bonny Ibhawoh)认为,在“可诉性及可执行性”方面,“发展权”的概念在联合国的发展受限,但其话语产生了一石二鸟的影响:使得中国既能够挑战其眼中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不平等,又能够保卫其主权及国内现状。因此,“发展权”这一概念在国际论坛中不仅是“矛”,也是“盾”。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努力,试图在联合国体系内影响人权的定义,比如其在201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有关“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的决议。法律学者米凯拉·萨拉马汀(Mikkaela Salamatin)认为这一决议有利于中国强调通过“合作共赢”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人权。中国政府强调人权最应从国内层面进行应对,萨拉马汀总结道,最终“打着支持普遍尊重这类权利的幌子动摇了对基本权利的推动”。
受援国的权利话语
然而,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其关注的主要是全球论坛的话语斗争,很少考虑那些接受中西方援助的国家内,比如缅甸,是如何展开对人权含义的争论的,以及中国相较之下对“发展权”的重视又如何在那些国家内发展。若作出假设,例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发展权’争论的动态以同样的方式在受援国展开”,就是错误的。
那么,传统的援助项目和更加强势的中国援助项目,是如何影响在联合国机构和全球组织内部,以及在受援国中关于权利的讨论?各援助国是如何力图说服老挝或柬埔寨等受援国的行动方内化符合本国偏好的人权含义的?
自冷战结束后,西方援助国对于受援国采取了一种明确的“干涉主义”方式。在近几十年来,民主、人权、治理得当及问责的概念一直是世界上大多数西方援助国国际援助项目的核心,在这些概念的含义及规范价值方面具有广泛的共识。
西方援助国最明显且直接应对人权话语的方式是通过援助项目体现的,譬如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民主和人权计划旨在“在人权及基本自由最受威胁的国家与地区中加强对这二者的尊重”。
各人权及倡导组织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及英国援助基金会(UK Aid)等援助方直接资助,人权领域的领袖会获得援助国交流访问、奖学金以及培训的机会。同时,在协商较大型的西方资金援助机制,以及与受援国进行双边协议时,往往伴随着附加条件,即在受援国的政策及项目中加入人权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援助国对受援国内地方人权话语进行的干涉,及其为发展人权的特定含义在全球作出的努力,这两者间的联系往往通过资金支持的生态系统得到明确体现,即双边赠款以及向联合国机构及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给予援助支持。
反之,中国援助对受援国内人权话语产生的影响较为不明显,但同等重要。从某种层面来说,中国援助行动方极其谨慎,避免受到对受援国行动方施压的指控。习近平在“一带一路”论坛开幕式中,表示中国“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
但尽管中国政府强调不进行“干涉”,中国能够通过一些关键机制对受援国的人权含义产生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成员国内进行的人力资源发展及专业化培训在传播符合中国式发展模式的准则方面有着关键作用,比如CIDCA于2021年1月宣布为缅甸医务人员提供为期两年的培训项目。如之前所述,中国在援助白皮书中高度重视“人文资源”这一维度。通过资助奖学金,到中国进行的交流访问,或是为受援国政府官员或记者提供的短期培训(都在东南亚开展),中国援助就能够转变受援国内的发展含义,使其向中国政府的偏好靠拢。
在考虑中国援助活动对亚洲人权含义产生的影响时,除了主要的中国政府行动方,研究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也至关重要。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中国外交中关键的利益团体,比如云南省省政府在中国同缅甸协商能源管道以及经济发展合作时就起到关键作用。人权的含义不仅是通过中国发展项目与受援国的互动(如进行培训和交换等活动),还通过中国各级政府渗入受援国话语中,而各级政府的人权话语可能各不相同。
最后,在考虑中国及西方援助机构在受援国产生影响的这些模式外,了解地方级行动方机构在人权含义相关的话语斗争中起到的作用也极其重要。地方政治及人道主义行动方在塑造中国及其它国家援助项目规划的结果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地方级行动方、机构和利益之间,更大型的地缘政治及经济竞争以微妙、混乱及矛盾的方式“实地”展开。例如,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马来西亚实施时,马来西亚政府及地方级行动方的权力在决定这些项目的成败上就至关重要。
增强对话语争论的敏感度
对于西方援助国而言,再回到曾经在国际论坛上主导人权、民主及问责等术语用法的时期是不可能的。随着CIDCA的成立及白皮书的发布,中国政府在援助领域影响越发突出的趋势已十分明晰。通过“人文资源”发展以及资助受援国的培训、交流访问及奖学金,中国“发展权”的观念将愈发挑战到其它援助国对个人民主及政治权利的重视。
因此,在对中国援助的崛起及其对于全球援助架构的影响进行新研究时,就必须更加关注受援国不仅作为地缘政治及经济定位的场所,还作为人权含义的话语斗争之地而存在的方式。我们必须变得更加适应这些话语争论,以此了解各种各样理解人权和实现人权的方式。
图片:2020年仰光的公寓建筑。 图源:Metro Centric/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