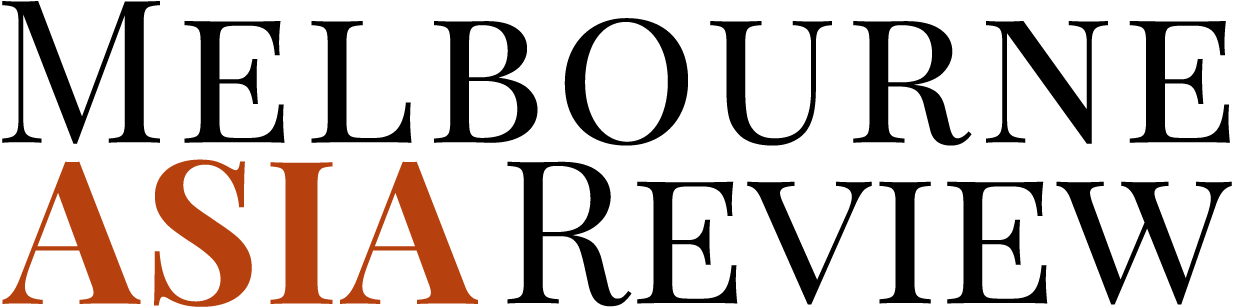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方子玥,黄紫楚,雷妤茜,李永霞
我们与日本在经济、战略以及文化领域上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过。在教育体系内,从小学到高等院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学习日语产生浓厚兴趣。但是,除了动漫《鬼灭之刃》和《精灵宝可梦》外,还有什么引起他们对日语的兴趣呢?而这些又是如何帮助大学开设有效且参与度高的语言课程呢?
日语是世界各地高等院校所开设的语言课程中最受欢迎的亚洲语言之一。根据《2018年海外日语教育调查报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20年),日本境外学习日语的人数达到385.1774万人,创下了历史第二高的记录。同时,自该基金会1979年的调查以来,院校和教师的数量也迎来了历史新高。尽管新冠流行,日语课程的注册率仍然相对较高,甚至在2021年依然如此。全球每10万日语学习者中,大洋洲所占人数最多,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主。
然而,作为本文作者,我们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高级日语课程的可持续性——特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
语言教育政策(政府和院校层面)的实行及高等教育部减少对语言教育的投资,使许多日语研究和日语语言课程面临压力。高级学科的注册人数通常比初级和中级学科低,因此这类课程最可能被合并、减少,甚至取消。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外交学院(FSI)认为日语是 “超高难度语言” 之一;相较于法语和意大利语,英语母语者需要投入三倍的时间学习日语,才能达到同等的 “专业工作能力” 水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学生的长期投入(直至高级水平)、有力的支持和高质量的教育,上述三个国家的致力于培养高水平日语使用者的日语课程就不会有可持续的未来。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最近启动了高级日语教学网络项目(上級日本語Network),并得到了2020年日本樱花小额基金会的支持。该项目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调查和访谈来收集数据,以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大学高级日语课程的现状,并倡导社群实践和整个行业持续支持。这一合作也涉及英联邦成员国。这些成员国的大学不仅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而且在课程设置上也有相似之处。
2020年,高级日语教学网络项目联集结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大学的同事,共收集了25所院校(澳大利亚19所、新西兰4所、新加坡2所)日语课程的数据。总共有76名参与者参与调查,在这些受访者中,有38名教师(34名来自澳大利亚,2名来自新西兰,2名来自新加坡)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间参加了线上访谈。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大众对 “高级” 水平的宽泛定义大致如下:
- 院校的发展现状;
- 能力水平评判标准与其他非日语语言的评判标准保持一致,如日语能力测试或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 通过参与各类学习活动或课堂练习(如通过语言课本学习)来展示特定技能
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院校教育体系对 “高级水平” 涵盖范围的定义是不同的。虽然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与欧洲语言进行的比较,但这些定义深刻影响着院校对日语课程的支持程度。
如果院校仅支持教师所定义的中级语言水平教学,那么我们就很难培养出高级日语使用者。我们发现,有些内容和学习资源较为相似的课程(比如使用同一本教材),被一些大学定义为 “高级”,而有些大学又定为 “中级”。通常来说,在一个三年制的大学学位课程中,从初学者开始的学生可以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提升到 “高级” 水平,但在很多情况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 “高级” 水平的学习仍然被高等院校的日语教师认为是 “中级” 水平的语言学习。在我们调查的院校中,大多数学生在学期内通常每周有三到四个小时的课程(最多五到六个小时)。这使得他们每年平均约有100课时,三年本科学位课程中,总共需完成约300课时。显而易见,这相较于上述FSI的评估而言课时不足。FSI评估认为日语水平达到 “专业工作能力” 等级需花费2200课时(法语和西班牙语为600-700课时,德语为900课时)。此处的 “课时” 是指课内学习语言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到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大学生选择课外语言学习。例如,学生完成混合交互学习中的线上作业,观看日剧或者参与其所在国家的研究项目。
除此之外,本项目还发现语言教学中存在一种趋势,即亚洲语言教学在逐渐适应欧洲语言教学框架。 譬如,大学常见的做法是将每种语言分为1-6级,其中5-6级定为 “高级”。这种分级忽略了一点:学生对不同语言的掌握速度各不相同。同一官方认证的 “高级” 水平下,学习日语课程的学生,其语言掌握程度很可能低于学习欧洲语言课程的学生。该项目共涉及三个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受英国的语言教育传统影响,在英语环境中运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语言(与英语共用基于罗马字母的书写系统)往往在教育体制中享有特权。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积极推动包含日语在内的亚洲语言教育。同时,两国政府坚持履行对多元文化的社会责任。例如,澳大利亚出台了多项战略计划。其包括1995-2002年间签署的《澳大利亚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学习战略》和2012年《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中关于亚洲语言研究的建议。新西兰政府于2014年推出了 “亚洲语言学习” 计划,承诺五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这一计划旨在通过开设新的亚洲语言学习项目或加强现有项目为学校提供教育支持。为满足教育产业需求,新加坡教育部于1978年建立了外语中心(现扩建并更名为教育部语言中心),为中学生提供法语、德语和日语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各大学及理工学院亦开设了日语课程。
如果不那么以欧洲为中心,少些以英语为中心的单一语言思维方式,就可以更好地支持亚洲文化的发展。2021年5月,一篇关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院校语言课程及评估现状的文章表明,学习法语等欧洲语言比学习日语和阿拉伯语更有优势,而这恰恰反映了上述偏见。此外,英语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对其它语言接受度不高。尽管学者香农·梅森(Shannon Mason)和约翰·哈杰克(John Hajek)认识到,语言为促进 “国家多语言化、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提供了重要途径,但媒体对语言教育的报道,内容肤浅、范围狭隘且充斥着消极言论,这往往会加剧澳大利亚语言教育岌岌可危的境况。
“高级” 日语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各阶段教学相互衔接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高等教育中,并非人人都是日语初学者。那些在学校学习过日语,或者具有日语学习经验的高校学生,不管是以正式还是非正式方式学习,都会选择从日语课程中第二或第三学年的进阶科目开始学习。大学三年课程结束时(新加坡通常为四年制),这些学生能达到较高日语水平。我们的受访者经常提到,长期对日语教育进行跨高校投资对于维持和加强熟练程度非常重要,其中包括在日本国内进行长期或短期交流学习的重要性。
然而,在加强教学衔接上有两个巨大阻碍。首先是结构性问题:随着本科学位课程的选择越来越有限,学生几乎不能灵活增加语言课程,甚至在选修课程中也是如此。在澳大利亚,由于学费越来越昂贵(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此外,尽管语言类学位学费低,且语言属于准备就业型技能,但学生仍然放弃了语言类课程而专注于他们的学位学科。有规律的持续学习对于语言学习十分重要。如果限制学生对语言课程的选择,可能会对学习产生反作用。在所调查的院校中,日语课程通常只是学生的 “选修课”,所以,无论大学日语课程项目为在校日语学习者提供的科目多么有吸引力,学生的日语也不一定能达到高级水平。
第二个阻碍则是语言在中学阶段的地位较低。根据澳大利亚统一课程考评与报告管理局(ACARA)的数据,2019年澳大利亚仅有10.3%的12年级(中学最后一年)学生选择学习语言。可见语言学习在中学最不受欢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报告还指出,澳大利亚中学阶段,学习日语的学生以及教授日语课程的学校数量减少,其部分原因是日语被中文及理工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所取代。而这一趋势在新西兰并不明显:由于中文科目在中学阶段课程设置里并不突出,且学生普遍认为理工科很难,于是很多都选择了相对简单的人文学科。然而,2020年13年级(中学最后一年)仅720名学生学习日语,自2010年以来减少了18.8%。新加坡由于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外语教育所处环境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所不同,其日语教学主要面向母语为中文或小学学过中文的高水平学习者。
高级日语教学的优势
我们的项目在学生网络、社群参与及全球公民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项目中许多老师为高级日语阶段的学生提供了机会,帮助他们成为日语使用者,成为能够批判地看待和对待新问题的世界多语言公民。在高级日语教学阶段,学生能接触到大量的真实资料。除了日本相关的当代社会议题,老师还会挑选全球热点话题作为研究。尽管这类话题需要定期更新教学资料和活动,整个项目的老师仍愿致力于促进学生对当代日本的了解。许多日语课程还积极展开合作活动,学生的合作对象有日本大学生和大学所在日语社群,活动中学生能够与来自各个地方、各种类型的 “日语使用者” 交流,而不仅限于日语母语者。部分老师还表示,得益于视频会议工具,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学生能通过在线学习参加大学日语课程,而不必在特定的地点线下上课。我们还发现,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人积极参与混合交互学习,使用在线交流工具,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日语使用者进行深入交流,以此促进日语学习。
参加我们项目的老师发现,学生学习日语是出于综合动机,而不是工具型动机。换句话说,学生是发自内心地对语言和文化感兴趣,而不是为了日后的求职。老师们多次表示他们的学生只是 “喜欢日语”。这与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调查结果一致:大学生学习日语的诸多动机中,排第一的是 “想了解日本流行文化”,其次是 “对日语感兴趣” 和 “在日本学习”,而 “未来就业” 排第四。部分老师还认为,学生可能对JET项目(日本政府支持的外语指导等外国青年聘用项目)的语言助教一职感兴趣,有在日本教授英语的意向,因为他们希望在日本生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职业目标。也许学生并没有把日语当作工具,来谋求以日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工作。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师还提到,对于具备日语能力的毕业生而言,跨国公司和咨询公司比日本企业更有吸引力。
我们采访中出现的一个主要共同点是,绝大部分日语老师的立场是对学生——“日语使用者”——的学习起到促进提高作用。无论学生已掌握了多少日语字符、语法和词汇,许多老师都会组织涉及现实问题及真实日语对话的活动,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独立、积极且具有批判思维的日语“使用者”。在项目中,我们鼓励三个国家中日语高级阶段的高校学生批判性地看待教材,用日文写出自己的作品,以便在课堂活动以及测评作业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在新加坡的一个课程项目中,学生首先批判性地阅读新闻报导、进行小组讨论,然后根据自己开展的日语采访写报告。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澳大利亚,学生借鉴日语“内”和 “外”的概念研究移居、社会边缘化和社会认同感的相关话题。来自该国一所大学的老师分享了一些由学生研究项目组选定的课题,其中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通枢纽,“无现金社会” 以及日本无性伴侣等。新西兰一所大学的老师与来自韩国、日本以及菲律宾的老师们共同组织了一场线上日语 “世界咖啡屋” 活动。参与活动的学生们本着 “世界咖啡屋” 有序但不乏轻松的风格,以小组的形式讨论具体的话题,老师们试图引导学生从日语学习者转变为使用者。
我们对发现这样的日语学习方法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中,毕业生的主要特征都包括具有批判性思维、成为独立且自主的学习者以及积极向上的社会公民。未来雇主高度重视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许多高校正在引入 “工学结合”模式。但是,近年来,大学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培养 “准备就业型” 毕业生,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现为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和劳动关系部)最近决定将语言学习纳入 “毕业生就业准备一揽子计划(Job-ready Graduates Package)”的课程范围内,这一举动应证了该趋势。这种对语言教育的功利主义看法已经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语言教育政策。其假定了语言研究的工具型动机,尽管在高等教育中,日语课程的学生和老师更倾向于日语学习的综合动机。
在我们项目中,高等院校的日语老师帮助高阶日语班的学生发展成为 “独立自主、积极且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语言使用者”,学生能够在课堂内外运用他们自身独有的一套语言积累,以及文化和知识上的储备。但是,在我们所讨论的三个国家,高校和政府的立场是把语言学习的工具型动机放在首位。
语言教育朝何发展?
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大学和老师通过高等语言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目前的教学朝何发展?目前高校和政府的立场对日语教学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需要具备怎样的语言和社会文化能力,才能更好地将学生培养成有具有全球素养,并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目标的人?
我们的研究项目成员注意到进一步了解学生学习日语高阶课程的动机颇为重要。澳大利亚日本研究协会(JSAA)已获得资助,开展另一项名为‘学生动机:为什么要在大学里继续学习日语高阶课程?’的研究项目(2021年由日本樱花小额基金会资助)。
Melbourne Asia Review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passing of Professor Hayes and the impact her work had on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Australia.
图片来源:昆士兰大学 ICTE/Flickr。图片已被裁剪。
原文链接:https://www.melbourneasiareview.edu.au/are-advanced-japanese-language-programs-sustai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