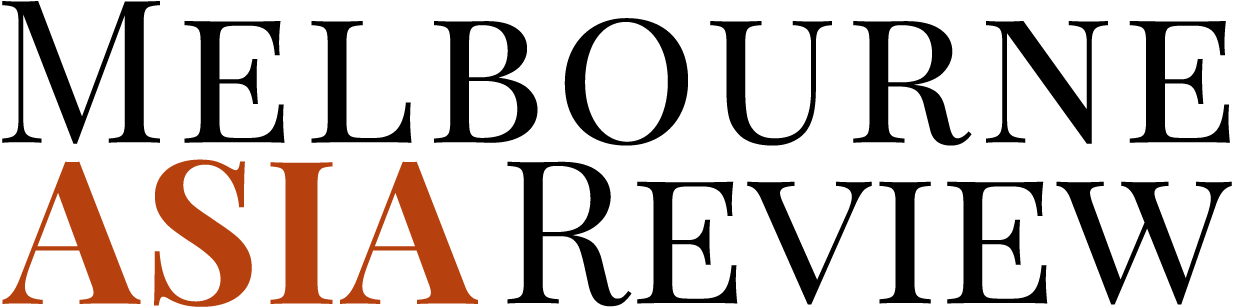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戴小瑾、李艳、郑玲美、张瑶
2020年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战后美国的历史上颇为少见。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的分歧是全球性的和跨议题的:气候变化、多边主义、贸易、联盟、朝鲜、伊朗、以色列、世卫组织……这个名单不胜枚举。讲得极端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内在驱动力就是反对拜登(其长期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占据席位)所代表的的几乎所有政策:这是美国两党在外交政策中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拜登惊恐地目睹了特朗普执政四年来的外交政策,他发自内心地否定近乎所有特朗普相信及代表的外交政策。这两种外交政策方针之间分化的逻辑是深层次的、个体化的,也是由他们对美国就所承担的世界角色方面极大的认知差异所驱动–这种分歧可以追溯到国家早期,并在其历史上多次重演。
在美国政治传统中,拜登是传统政治信仰的拥护者,即美国的建立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它目前所持有财富和权力已证实美国价值观乃永恒真理。伴随着财富和权力而来的责任就是“领导力”——这是最能够准确描述拜登外交政策纲领的一个词语。对拜登而言,没有美国的领导力就没有美国的伟大,一个无法再领导世界的美国则无法定义为“伟大”的美国。
特朗普对美国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美国是由一群致力于摆脱旧世界的肮脏政治和竞争的人民组成而来。对美国来说,因再度陷入这些竞争和肮脏交易中而导致的腐败是其价值观和制度面临的威胁。在特朗普看来,要复兴美国之伟大,就必须退出由误入歧途的前任总统们领导加入的所有协议和组织,譬如多边组织、联盟和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认为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主义理想是一种错误意识,这种意识让其他国家剥削、侵蚀和削弱了美国。特朗普在任何时候都优先考虑美国的得失,并不关心邻国、盟友以及合作伙伴需要承受何种后果。
11月3日的美国大选结果对亚洲来说意味着什么,答案在某种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特朗普获胜,我们将重蹈覆辙:反复无常地关注或参与某一事务、专注于峰会协议的达成、迫使盟友付出更多,以及放弃区域贸易协定而追求对美国有利的双边协议。如果拜登获胜,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外交政策:自由国际主义、尊重盟国并展开合作、对独裁者态度强硬,以及广泛的地区主义。
但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在国际事务中,危机隐藏于细节之中。即使美国总统持有强有力的观点,也可能被细节所迷惑。下面是两位候选人都将面临的一些关于亚洲的复杂情况。
中国
在特朗普和拜登的两极分化外交政策中,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在中国问题上,两位候选人的立场几乎没有区别,这反映出美国两党在对华问题方面达成的共识日渐增多。特朗普通过激烈的贸易战和关于“中国病毒”的阴阳怪调抢占了头条,但美国对中国有增无减的敌意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便已存在。在特朗普入驻白宫之前,美国政府对北京当局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的愤怒、对其外交政策的警惕、对其遵守国际规则的质疑、及对其间谍活动的怀疑至少已经持续十年之久。
无论是谁入驻白宫,如何应对中国都会是一个难题。特朗普以及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他似乎主张策动北京当局的政权变更)的激进做派,将注定面临各种困难。显而易见,此举并不奏效。然而特朗普的强硬姿态除了在贸易上让中国作出了些微让步,并未取得什么成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在美国所担忧的行为上作出任何让步——对内推行威权主义、对外保持强硬态度。第二,中国可能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小的主要经济体,而美国的经济或将陷入困境。特朗普的贸易战措施是否能让美国从深度经济萧条的泥潭中挣扎出来?第三,尽管特朗普许诺了会与朝鲜达成协议,但由于平壤方面在坚持推进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朝鲜问题正在持续恶化。如果特朗普想要重回谈判桌,北京将会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拜登的对华政策存在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尽管许诺会与北京建立更加务实的关系,他依旧想要利用美国在民主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来迫使北京改变做法。这是拜登想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段达成的实际目标。此外,大多数候选民主国家和准民主国家对抗衡中国兴趣不大。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都明确表示并无意愿加入特朗普和蓬佩奥的对华舆论战。拜登希望这些国家此举是由于特朗普的逼迫,而非出于任何务实的原因。但其实这种想法是脱离经验判断的。
地区主义
早在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之前,亚洲独特的地区主义就已经面临衰落的风险。虽然年度峰会及其筹备会议仍在进行,但议题的实质和达成的协议则越来越老套乏味,而且与威胁该地区的实际挑战相去甚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盟和中国之间就南海问题意愿达成的行为准则,该准则在谈判开始前就已经停滞,双方通过法律声明互相交锋,航空母舰也在争议水域相持。
特朗普的上台和他粗莽的行为引起一种预期, 即随着对美国的信任动摇,亚洲地区主义将收紧。但到目前为尚未出现这种情况。于2018年12月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ATPP),或许可以视为美国退出后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进展。
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像第一任期一样对亚洲的地区主义不屑一顾,他能否担得起这个责任。首先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担忧,即如果美方持续保持漠不关心,中国是否会取代其领导地位。特朗普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为让习近平有关“亚洲的安全要由亚洲人拿主意”的论点增加了砝码。中国对地区领导权的主张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美国不可靠、地区制度正在被侵蚀以及自身利益。北京不可能找到比特朗普更好的例子了。考虑到南海问题,特朗普可能需要更加严肃对待亚洲的地区主义。仅是玩玩海上边缘政策的把戏并不能威慑住中国。如果东盟默许北京的主张,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严重的战略挫败。所以,通过地区组织提供保障可能会变得愈发重要。
拜登希望恢复特朗普上任之前的外交政策。一个富有象征性意味的姿态就会是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重新加入该协定可不像朗普退出那样容易了。该协定经过各种艰难的双边谈判才得以达成,美国谈判代表经常需要为此做出极大的努力。CPATPP的成员国是否真的有勇气对华盛顿的贸易特使作出更多的让步?其次,恢复美国在亚洲的可信度问题,要知道,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在亚洲的信用就已经在逐渐降级。2012年,奥巴马政府决定,不支持菲律宾就美济礁问题上与中国对峙,这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对于美国打压中国的信心,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再加上特朗普四年期间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都在寻找其他方法加强自身的安全,以应对崛起的中国。军火进口量猛增;截至目前,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这几个相距甚远的国家,也已进行安全合作。对拜登来说,扭转这一趋势,并使美国再次处于领先地位,将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盟友
全球联盟比任何政策框架都更能明确地定义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依靠与多个国家达成深层而稳定的安全协议打响冷战,并依此在苏联解体后稳定了全球化的世界,同时保住了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美国最重要的盟友除欧洲国家以外都在亚洲,他们维系着世界范围内局势最为多变的地区——亚洲的发展与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本世纪的修正主义大国会如此热衷于想要削弱美国的联盟,以便削弱美国本身。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21世纪白宫的三任领导人都曾对他们“施以过援手”。
因此,难怪拜登将联盟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对拜登而言,联盟构建的框架能助力美国重新确立领导地位,因为他认为盟国是最能接受美国价值观和领导力的国家,他们奠定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价值观联盟基础。对拜登来说,坏消息是,如果他赢得选举,他将接手美国在许多最重要联盟核心的信任赤字问题。在他之前的三届执政班子——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倾向于以类似削弱盟国在其领导人和公众眼中的价值的方式来对待其盟国。小布什对那些不支持他入侵伊拉克的盟国展开攻击,这有力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即在单极化的情况下,盟国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联盟现在意味着不容置疑的忠诚。奥巴马冷漠地对待盟国,把维护联盟的大部分重任留给了拜登和他的国务卿们。而特朗普则指责盟国在敲美国竹杠的时候是排头兵。
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在第二个任期突然改变对待盟友的态度或做法。日本和韩国首当其冲,遭受了他的欺凌和威胁,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应付了他的第一个任期。但他们对美国的依赖是一项递耗资产。如果美国总统想利用这种依赖作为杠杆与其盟国达成更好的贸易交易,或者说如果美国国务卿一心想要凭借这种依赖逼迫其他国家孤立中国,将很难奏效。
在国际事务中,就如同生活中一样,你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每位总统在赢得选举上台后所面对的世界和前任总统,自然是不一样的。2020年尤其如此,因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根本政策完全不同。欧洲和亚洲,这两个地区在冷战期间对美国尤为重要,但他们在过去的四年间已经在加速脱离美国的影响。他们不再一位依赖美国及其领导地位;相反,这些国家开始注重独立自主和实用主义。
相较于2016年,2020年的亚洲更需要美国,却更不信任美国。美国和亚洲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对次拥有足够认识、并相应调整美国对亚政策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可惜的是,目前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对美国在世界承担角色的认识虽然大不相同但都颇为过时。而美国民众只能在二人而人们不得不在这两位候选人之中做出选择。亚洲的战略形势在急剧变化且不可预测;特朗普或拜登需要迅速理清这一点,否则世界将面临另一个动荡的四年。
本文的精简版本同时刊载于《南华早报》,未经《南华早报》许可不得转载。
图片: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图片已被裁剪)
原文链接:https://melbourneasiareview.edu.au/trump-or-biden-the-implications-for-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