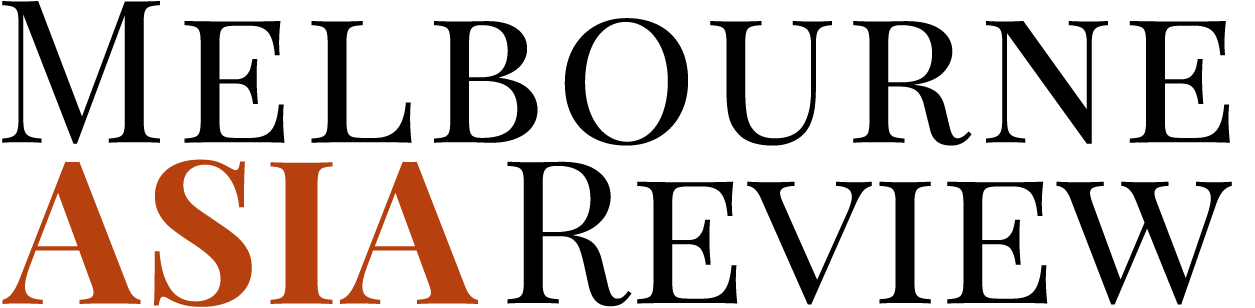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逯佳欣、郑微潞、李玥琦
从本质上说,归属感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空间的美好愿景,在这个空间里,个体差异不会成为阻碍自己与他人产生联系的壁垒。一些人将归属感和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情感安慰的渴望联系起来,这种渴望建立在认可、联系和/或接受的感觉之上。它通常是一种社会情感,即与一个群体的亲近感,成为比自己更大的群体的一部分,并受到他人的欢迎。我们中许多人是在家中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并试图在不断拓展的社会圈层中重现这种感觉,包括学校、工作场所、我们生活的圈子和我们所在的社区。
幸运的话,生活中大部分时刻你会产生归属感。虽然在某些时间点,我们所有人感觉像“离开水的鱼”,特别是在全新的文化空间中,这种良性无归属感的体验是一种暂时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很少能够感受到。
相比之下,不幸的话,其他人有意无意,有时甚至蓄意让你感觉“不自在”。从公开暴力和欺凌行为到更微妙的职场歧视,日常生活中的不正当对待和社会排斥,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恐惧症、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残疾歧视都会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产生无归属感。这种歧视可能表现为缺乏认同感或感到不适,甚至发展到被极力妖魔化,乃至让人受到暴力威胁。与偶尔的良性、短暂性的无归属感不同,这种无归属是由阻碍或侵蚀特定群体归属感的系统性行为造成的。我认为“无归属感” (“unbelonging”)中的“无”(“un”)是指主动破坏某人的归属感,破坏他们的社会联系感,有时甚至是安全感。
对于那些经历了无归属感的少数群体来说,身份政治是其避风港。在身份政治之下,受打压的少数群体享有共同的经历,由此产生了“群体”的概念,这一概念取代了来自家庭、地区或国家的无归属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青少年时期相信,当我最终成为同性恋群体的一员时,我会感到完整。面对来自家庭、菲律宾群体、天主教堂和学校的恐同情绪,我由衷地相信,一旦我成为同性恋群体的一员,我最终会在某地找到归属感。
然而,正如我之前写过的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同性恋经历一样,我骤然觉醒。我在澳大利亚同性恋群体中所经历了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十分刻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普遍歧视,我从未想到对此会如此震惊。当时,亚洲男同性恋者被禁止进入同性恋场所,酒吧服务人员拒绝为其服务,舞池的某些地方不允许其进入。在某些场合,别人向我吐唾沫,咒骂我,将我绊倒或推下楼梯,我还经历了性羞辱。无论是在在生理、社会还是情感层面,亚洲男同性恋者都认为自己并不属于澳大利亚同性恋群体。
无处不在的性别种族主义
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明显的社会排斥行为和性排斥行为已经从如今的澳大利亚同性恋文化中消失了。虽然这些行为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很少见了,就算出现也会受到批判。这表明一些社会共识在发生变化。但是,性别种族主义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其含义是:基于种族刻板印象和特征,要么将男性排除在约会和性生活之外,要么将男性纳入其中的行为。进行网络约会和使用约会应用程序时,性别排斥在用户的约会资料上得到了更明确地显示,按种族和民族筛选潜在约会对象的功能也得到引入。虽然一些同性恋群体约会应用程序如Grindr已尝试取消种族过滤功能,并且禁止种族标签滥用现象,这些努力均未能阻止性别种族主义的蔓延。
人们要为这些行为进行辩护时,往往称其为无伤大雅的性偏好。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佐证,该研究表明,那些对某个种族有性偏好的白人男同性恋者(特别是不喜欢亚洲人的),则更有可能持有其他普遍的种族主义观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有种族色彩的性偏好就是种族歧视的体现,但这算是一种株连。正如后来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的那样,如果在某个时间点种族化性偏好不再与宏观上的种族主义观点密切相关,那么这种偏好仍然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吗?
正如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亚洲男同性恋者所认为的那样,性别种族主义本身就存在问题。当种族偏好建立在种族主义刻板印象和暴力的历史基础上时,性别种族主义就会产生。在他们的约会、性行为和交往中,让充满不平等和暴力的种族贵贱说根深蒂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白人男同性恋者是否也持有其他种族主义观点并不重要,因为种族主义本身就存在于他们的性和/或亲密行为中。
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性别种族主义男同性恋社区中建立了一种以渴望程度对不同种族进行等级划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澳大利亚同性恋文化中的亚洲男同性恋者是被贬低的对象。遭受性别种族歧视往往会导致自尊心下降,也会导致对生活的满意度降低。对亚洲男性的身体羞辱很普遍,而且往往与厌女症、种族主义和变性恐惧症交织在一起。例如,“亚洲男性阴茎很小”以及“亚洲男性毛发稀疏”这些刻板印象通常来源于错误的认知,即亚洲男人“孩子气”或女性化。在这种情况下,白人文化对美丽、年龄和性别的种种期望结合在一起,把亚洲男性描绘成缺乏男子气概的群体。一些男同性恋者认为亚洲男性只是“男孩”,他们对此十分失望。但其他白人男性同性恋者可能会推崇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们利用亚洲男性的男孩子气和/或柔弱来证明等级关系的存在,这种等级是他们强加于其性伴侣或固定伴侣身上的。
在一对白人和亚洲人组合的同性伴侣中,一种假想的性别角色设定总是强加在亚洲人那一方身上,他们扮演着两性关系中女人或者妻子的角色。他们不仅被自己的白人伴侣这样对待,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也被他们的家庭与社交网络普遍接受。举个例子,人们普遍期望亚洲伴侣能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特别是烹饪或者解决伴侣的性需求。在重要的人生决策上,比如未来的职业规划,或者将来的定居地,亚洲“男孩”可能被期许以他们白人伴侣的事业为重。
婚姻平等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进入了名为“同性正典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认为同性伴侣在模仿异性恋理想中的婚姻,而历史上,同性伴侣无法养育孩子,所以他们无法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随着同性事实婚姻的法律认可,同性联盟和婚姻的合法化,生殖技术权以及领养权的获取,这种诉求有可能实现。迄今为止,随着澳大利亚社会中同性权益和关系的日益正常化,同性恋社群中持续的种族主义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活跃着。
以澳大利亚的婚姻平等投票为例。婚姻平等支持运动旨在使同性婚姻在澳大利亚合法化。在媒体上的公开辩论中,支持者们以口号“爱即爱”(love is love)为核心,指出婚姻平等与跨种族通婚合法化的相似之处。支持者们直接借鉴了美国婚姻平等运动,后者经常引用1967年的“洛文夫妇诉维吉尼亚州”一案。该案件结束了反混血法律,作为扩大婚姻平等的先例。婚姻平等运动的另一个口号是“爱,无关歧视”。
然而,尽管支持婚姻平等的活动者们把跨种族通婚合法化作为支持同性婚姻的先例,但同时,澳大利亚的白人男同们却又积极践行着上述详细描述的性种族主义。换而言之,许多白人男同虽然支持反种族通婚和跨种族通婚,同时还将法案作为他们自己结婚权利的先例,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又实施性种族主义,将亚洲人强制排除在同性恋的浪漫和性生活之外。因此,强调异性恋跨种族婚姻合法化和同性婚姻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强调了从反异族通婚到性种族主义的种族排他性性实践的延续。
婚姻平等公民投票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支持婚姻平等的人中流传的一张梗图,要求观众考虑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会与哪些国家联系在一起。在“是”一栏下,他们列出了已经合法化婚姻平等的国家,绝大多数(除了巴西和阿根廷)是西方国家。在“否”一栏下,是不支持婚姻平等的国家。这里,他们将澳大利亚与来自亚洲和非洲大陆的国家列在一起,包括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表情包底部写道:“这就是你所处的国家”。表情包中没有实质性论证支持婚姻平等,但暗暗揭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羞耻,因为它把澳大利亚与这些被视为“落后”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这利用了历史上长期殖民对文明等级的划分。表情包激起了澳大利亚白人对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和文化的条件性种族厌恶,特别是对反恐战争背景下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并借此说服公众投票支持。
最后,当“赞成”阵营在公投中获胜时,美国广播公司选举分析师安东尼·格林声称,西悉尼的“反对”票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新南威尔士州是“到目前为止,非英语国家出生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在我们胜利的前夕,澳大利亚最受公众信任的分析师之一将“反对”票归咎于来自“非英语背景”的移民。对此,一些有色人种酷儿并没有庆祝,而是花时间应对指控。公共评论人士对移民为什么“反对”票如此高提出了解释,即落后文化、移民天生保守、村落心态。这些术语奠定了辩论的基础,即使活动家和进步学者试图为移民辩护。
虽然一项关于婚姻平等投票的研究表明,拥有更多“移民”或“多元文化选区”的选区对同性婚姻的反对更高,但“移民”被狭义定义为外国出生,非基督教信徒、近期入境来自非英语背景的新移民。这个研究将非基督教宗教、外来性、英语背景、移民身份和多元文化混为一谈。另一项对变量进行分解的分析表明,更显著的相关性不是出生在海外与“反对”票之间的联系,而是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与投“反对”票之间的联系。其他调查数据的进一步计算不仅证实了宗教信仰与反对同性恋权利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而且进一步佐证了宗教信仰抑制了教育、父母教育和城市居住的自由选择。
因此,正当澳大利亚的亚裔同性恋应该与同性恋社区一起庆祝历史性胜利时,我们作为亚裔却被毫不客气地作为政治敌人驱逐出了庆祝活动,仅仅因为我们来自“非英语背景”。我们被迫为自己和我们的社区辩护,并因此承担“反对”票的全部责任。事实上,在一些酷儿空间的庆祝活动中,白人直男盟友更受欢迎。同时,亚裔男同性恋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男同群体却受到怀疑甚至是仇视,这表明白人至上主义在澳大利亚婚姻平等辩论中的影响有多大。总的来说,澳大利亚的婚姻平等公投强调了亚裔同性恋其实很难融入到(以白人为主导)同性恋社区中。
性小众家庭
同性恋正典化时期的第二个关键基础是使同性恋家庭正常化,这些家庭模仿了白人、异性恋、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从历史上来说,同性恋社区建立了更为激进的“选择家庭”以填补许多同性恋者出柜后失去真正亲人的痛苦,例如父母与其断绝关系,被逐出家门。因此,早期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解放论者对核心家庭持高度批判态度,他们常常认为核心家庭是他们受压迫的核心原因。由于国家法律阻碍了同性恋群体效仿异性恋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同性恋群体被迫要去创造可替代的亲属关系和照顾网络。即使同性恋的关系被合法化,他们的关系仍然不被法律承认,且经常被禁止采用领养或人工受孕服务。
20世纪下半叶,随着男女同性恋获得权益后,白人中产阶级的同性恋伴侣开始模仿白人异性恋中产阶级核心家庭,这一现象在美国主流同性恋媒体和娱乐界尤为普遍,从而引发了一段对这种理想家庭形态的正常化时期。同性事实婚姻和同性婚姻登记的增长为越来越多想要孩子的人提供了更稳固的基础,包括通过代孕的方式。由于澳大利亚在法律上禁止商业代孕,想有孩子的同性伴侣需要在澳大利亚寻找无偿的代孕者,或者寄希望于国外的商业代孕。一些澳大利亚的白人同性伴侣已经转向亚洲的国家,例如,在印度、柬埔寨和泰国寻找有偿代孕者。
然而,跨国界、跨种族的代孕对于白人同性恋伴侣来说带来了新的问题。同性白人男性伴侣采用的是胚胎移植代孕服务,这意味着婴儿与代孕母亲没有生物学上的关系,这使得同性白人男性伴侣可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是白种人,同时,同性伴侣中的一位提供精子,是孩子的生父。这样的安排,无论初衷多好,都无可避免地利用了富裕的白人同性恋男性在过度发达国家雇用代孕者与贫穷的亚洲女性出租她们的身体以生产白人孩子之间的权力不平衡。跨国商业代孕是一个基于亚洲妇女子宫商品化来生产白种婴儿的商业产业,以确保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北方发达国家(即北方世界,包括欧洲、北美和亚洲发达地区的一些国家)中白人同性家庭的延续。怀孕到足月以及分娩的劳动,以及身体上造成的伤害,还有代孕所需要承受的身体风险,这些都外包给那些在性别、种族和阶级方面都没什么特权的人。
这与西方男性长期对亚洲女性的性商品化历史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背景下。虽然白人同性恋男性并没有将亚洲女性作为性欲商品,但他们确实将她们当成实现自己白人家庭的性生殖工具。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同性恋的白人男性将繁育劳动外包给亚洲女性,充满了利用亚洲人进行廉价劳动(又名“苦力劳动力”)的殖民历史色彩,这样的情况在当代全球经济中重复上演,即把亚洲人的身体(甚至身体部位)视为可交易的商品:从性旅游到医疗旅游,再到现在的代孕旅游。需要注意的是,亚洲女性子宫的商品化是将子宫出租来保证白人同性家庭的延续,这种外包生殖劳动的做法正好发生在对“亚洲人口过剩”的种族主义焦虑的全球背景中。
我知道一些同性恋亚洲男性并不关心这里提到的问题。许多人甚至积极参与这些实践,例如,针对其他亚洲人的性种歧视和使用亚洲商业代孕服务。但是这些实践在伦理和政治层面让我感到不安。就我个人而言,要处理这些困难相当困难,我真心地为我们男同性恋社区中一些人最终能够有孩子而感到高兴,也为我们拥有更广泛的繁育权感到开心,但是许多同性恋白人男性轻易地利用不平等体系为自己的家庭谋利,以及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表现的愤怒,都提醒着我应该把批判的目光移开。换句话说,作为澳大利亚同性恋群体的一员,我必须放弃团结更广泛的亚洲群体。
同性恋亚洲男性在澳大利亚男性同性恋社区中的归属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并且始终取决于我们被认为有用和“表现良好”的程度。有时我们的包容性会受到质疑,就像我们在婚姻平等公投之后看到的那样。有时,我们又被推出来证明澳大利亚男性同性群体的包容性,然后,在澳大利亚同性恋约会生活中,公然支持种族排他的做法却比比皆是。我们被用来丰富同性恋广告和LGBTIQ+组织的领导团队,但是,与白人民族主义相似,我们被视为永久的客人,出于礼貌,我们被要求不要提出有关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棘手问题。尽管我已经找到了一种与之共存的方式(我已经这样很长时间了),但我努力把这种困境称为“归属感”。
图片来源: Aiden Craver/Unsplash. (图片经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