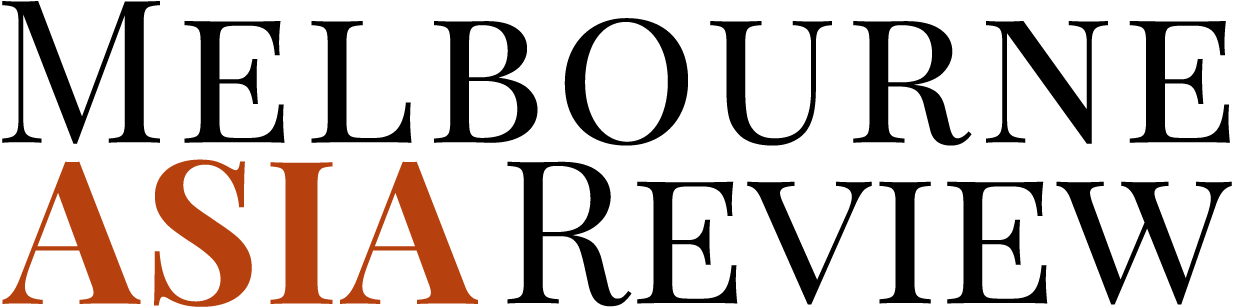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田沁、刘璇、陈思葳、黄展
二十世纪的一个美好设想是,在一个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推广一种共同的语言,可以增进合作和理解。
但我们一再看到,在创建、普及和施行通用的语言体系所需的权力结构的同时,会导致社会中某些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已经处于边缘化的群体。此外,统一的语言往往参与并加强社会和政治结构,很容易压制多元化的思想、表达和身份。
所有社会从本质上说都是多语言社会。接受并考虑这一事实比忽视或试图压制语言多元化更有成效;从长远来看,语言多元化可以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多语并用”(plurilingual)一词经常用于教育语境,但该词也有助于思考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一个比“多语并存”(multilingual)更为灵活的术语,多语并存可能意味着在不同的场合或由不同的人分别使用许多独立的语言。而多语并用则指语言的多样性,还指社群、机构和个人复杂多样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多语并用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说多种语言,而是说不应阻止任何人使用他们自己选择的语言。至关重要的是,与文化多样性和环境多样性类似,语言多样性可以增进社会关系,使社群和个人更灵活、更具适应力、更加多样化和更具包容性。
尽管支持多语言环境和多样的语言体验有其优势,但强大的机构、政府和意识形态(约瑟夫·洛·比安科 Joseph Lo Bianco)往往假定或宣扬单一语言的理想,从而给推动多语并用社会(plurilingual societies)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反之,也可以借助机构、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支持多种语言以及个人和社会使用语言的方式。
在处理多语并用社会涉及的紧张关系和机遇方面,澳大利亚具有代表性。尽管澳大利亚是包括原住民和移民在内的数百种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家园,无论意识到与否,使用单一语言和以盎格鲁为中心的观点仍持续地渗透到社会的某些阶层,特别是有权有势的精英阶层,影响着人们对多语言主义和语言学习的态度。目前英语在全球交流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
几十年来,历届政府一直强调,鉴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及与亚洲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反对以盎格鲁为中心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倾向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社会观念在阻碍学生学习语言(卡罗尔·海耶斯等 Carol Hayes et al.)。
只有当其他语言能作为工具或提供经济好处时,其他语言的价值才会在单语思维模式下得到认可。然而研究表明,积极参与的语言学习者往往由所谓的综合动机而驱动,其中跨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而非出于获得潜在的经济回报(大桥纯和大桥裕子 Jun Ohashi and Hiroko Ohashi)。积极地参与到语言学习中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但纯粹强调其工具型动机实际上可能会使学生脱离学习本身,从而失去语言学习中附加的经济效益,而这种经济效益正是工具主义方法有意要培养的。
新冠疫情凸显了对多语言读写能力的需求,也体现了在实施新冠防疫措施期间满足多语言读写能力需求的困难。
格雷斯·齐(Grace Qi)指出,与社会互动并体验到社群和身份认同之间复杂的联系会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尤其当语言能力会直接影响获取健康相关信息的效能感。复杂且持续变化的情况需要对语言细致入微的理解,因此实际的语言教学变得至关重要。渡部恭久(Yasuhisa Watanabe)讨论了在线上教学中设计特定活动以求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互动,从而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德维·诺维里尼·杰纳尔(Dwi Noverini Djenar)写道,语言间转换时,一对一的思维方式(通常被认为是盎格鲁中心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最大限度减少误解的方式,但这也可能会让人把事物想得过于简单并导致一些误会,从而掩盖文化和政治差异的复杂性。
在文化和政治形态差异下,翻译是复杂的,且难以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胡碚指出,就中国官方话语而言,得到中国共产党认可的译文都经由“文化滤镜”的处理,滤去可能有违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部分。她认为,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不应仅遵循单方向、自上而下的模式”,还必须考虑到跨文化交流发生的复杂环境。Delia Lin指出,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环境令人担忧,在中国,英语的世界霸权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偏见格外显著。放眼中东,“被接受”的翻译中缺失重要的政治层面的考量,而政治意识可以通过重新仔细考虑翻译过程得以增强。亚西尔·苏莱曼(Yasir Sulieman)以巴以冲突的案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主流翻译导致人们难以察觉一些不平等现象,隐藏了与主流视角抗衡的观点。
在该地区诸多地方,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导致小部分语言占据霸权主导地位。以巴基斯坦为例,乌尔多语为巴基斯坦国家范围内使用的语言,而英语则是官方语言,两种语言对巴基斯坦其他地区语言构成了双重威胁 (阿米尔·阿里和马娅·戴维 Ameer Ali and Maya David)。同时,乌尔多语支持者和英语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也暴露了经济差异 —— 精英阶层偏爱更高质量的英语授课教育,与之相比,普罗大众则接受乌尔多语授课的教育(侯赛因·卡德里 Hussain Qadri),而其他地区语言的母语者则并无机会接受第一语言授课的教育。
原住民语言使用者是最为边缘化的群体。近期,尼泊尔的民主改革涉及到原住民权利和母语教育问题,巴基斯坦也面临相同情况,精英阶层推崇的英语挤占着边缘群体获得母语教育的资源,让边缘群体更加处于不利境地 (Prem Phyak)。在台湾,和亚太地区其他政府一样,关于各种语言使用范围的争议在主张多语并用社会的政策中尤为显著,但是政策的执行总是困难重重(布雷特· 托德 Brett Todd)。
在上述例子中,原住民语言、国家语言和国际语言在叙事和意识形态上相互冲突。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清楚地印证了这种矛盾冲突, 群岛间语言的多样性常常相悖于国家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统一力量。 Justin Wejak 进一步回顾印尼社会的情况以及语言与身份的相互联结,尤其是在多语并用社会中,这不仅关于自我身份认同,同时也关乎个体如何定义与他者的关系。
“多语言主义的不平等”通常涉及某些语言不受重视,另一些语言得到重视。不受重视的语言常常是原住民语言,也可能是移民社群的继承语,或简单统称为“外”语。受到重视的语言如英语、阿拉伯语或中文等是区域通用语、国家语言或者国际语言。
一边提倡多语并用的优势,一边指出多语言主义的不平等,这看似矛盾,却正是关键所在。解决多语言主义的不平等并非要剥夺在主导语言下使用、推广和学习多种语言的机会。相反,要通过高参与度的教学,文化意识相关的翻译实践,或是支持社会中更多边缘群体的语言自决,在多语环境下创造和发展平等的机会。
图片:新加坡街市。来源:Brian Evans/Flickr
在发表后本文在原文基础上有作补充。
原文链接:https://melbourneasiareview.edu.au/the-contemporary-challenges-facing-plurilingual-socie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