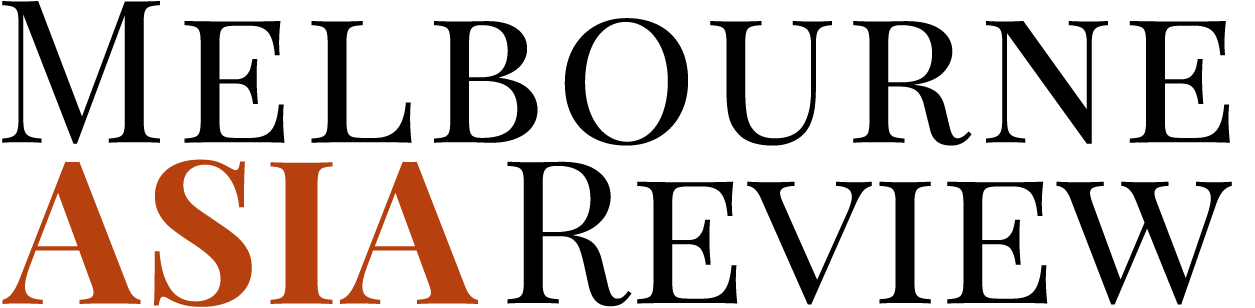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钟雨恬(Yutian Zhong), 陈志睿(Zhirui Chen)
蓝色安全(Blue Security)/墨尔本亚洲评论(Melbourne Asia Review)的“南海以外:东南亚其他海洋争端”特刊,为众多未解决的东南亚海洋边界争端提供了背景和清晰的解释。本特刊旨在讨论和剖析备受关注的中国南海九段线争端以外的地区性海洋边界争端。由于当前东南亚海域的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十分紧张,对于申索国和整个地区来说,成功且及时解决所有地区性海洋争端至关重要。本特刊旨在提出积极举措,以加强地区的海洋秩序。
“蓝色安全” 特刊特约编辑:助理教授贝克·斯特拉廷(Bec Strating)、特洛伊·李-布朗博士(Dr. Troy Lee-Brown),以及墨尔本亚洲评论的主编凯茜·哈珀(Cathy Harper)。
蓝色安全(Blue Security)是拉筹伯大学亚洲研究部(La Trobe Asia)、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简称GAI)、西澳大学国防与安全研究所(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s Defence and Security Institute,简称DSI)以及亚太地区发展、外交和国防对话(Asia-Pacific Development, Diplomacy and Defence Dialogue,简称AP4D)的合作项目。本项目为印度–太平洋地区读者撰写有关海洋安全的工作文件、评论文章和学术文章。蓝色安全的资金支持来自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
肯·布斯(Ken Booth)于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结束后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位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其著作《法律、武力和海上外交》(Law, Force and Diplomacy at Sea)中写道,“海洋的领土化” 将确保 “海洋将被视为陆地的延伸……各国将会十分在意并想捍卫这些土地,这实际上是爱国情怀的体现”。
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海洋边界争端,往往不似中国南海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些争端不时占据当地新闻媒体的头条,甚至引发公众抗议。人们因海域而爆发爱国情感,通常会给东盟(ASEAN)地区政府拉响警钟。东盟引以为豪的是,避免了激烈的国际冲突,确保了稳定的区域国际秩序。当边界问题引发人们民族主义自豪感高涨时,政治领导人可能会难以抵制公众压力,对所谓富有侵略性的邻国表现出坚决态度。各国政府一向热衷于悄然处理未解决的海洋争端,除非政治领导人认为在其国内议程上提出共同的国家事业会带来好处,
本《墨尔本亚洲评论》特刊,为众多未解决的东南亚海洋边界争端提供了背景和清晰的解释。来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专家,特别关注那些正式与非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在处理甚至解决重叠的海洋权利主张方面发挥了作用。通过贯穿本期所涉案例的几个基本主题,本刊为对东南亚海洋区域进行划界的成功与失败尝试提供见解。
第一,这些文章表明,尽管某些海洋主张可能被认为太过激进,但争端通常并非地缘战略竞争、侵略性,甚至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表现。相反,争端是海洋划界复杂性的表现。东南亚有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群岛国家,即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两国对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海洋权利和权益亦产生了影响,这加剧了其海洋划界的复杂性。各国都十分了解海洋权利主张重叠的原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学会了与之共存。正如塔瑞希尼·克里希南(Tharishini Krishnan)在本刊中所解释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已经为临时管理制定了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泰国湾(Gulf of Thailand)等地建立联合开发区。在另一些情况下,正如杰伊·L·巴通巴卡尔(Jay L. Batongbacal)的文章所述,政府只是避免了在彼此认为属于己方的区域进行活动,例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未划界区域。
其次,这些文章明确指出,海洋划界通常需要时间,特别是在地理上邻近多国的区域。划界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之间存在争议关系。有时,某个区域划界被搁置,是因为其取决于不同两个国家之间边界线的划分,正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曾在马六甲海峡东部的情况一样(见莱昂纳多·伯纳德的文章)。当海洋边界争端与主权争端交织在一起时,除非后者得到解决,否则不可能就海洋区域达成明确的协议。这也符合菲律宾历史上对马来西亚控制下北婆罗洲(Borneo)的主张。尽管该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暂时搁置的状态,但也将影响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西里伯斯海(Celebes Sea)的边界线划分进程(见本期巴通巴卡尔的文章)。在中国南海,东南亚的主权申索国因尚未与中国就司法管辖权与权益达成协议,迄今为止基本上已淡化了各方的争端。这里主要涉及到越南,越南对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各小岛的归属有异议,这些小岛目前被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占据。并且,两国之间还存在重叠的环礁权利主张,越南对此也有异议。
第三,正如贝克·斯特拉廷(Bec Strating)和特洛伊·李·布朗(Troy Lee-Brown)提出的海洋争端解决框架所证明的那样,海洋领域的分歧并不仅仅涉及经济利益、民族主义姿态或国际信号,而可能是各种因素共存。通过区分争端类型、权力不对称/国家认同和争端解决等,该框架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以全面理解争端的复杂性,并从多种情况中得出相关经验教训。
专业知识(Know-how)
实质上,解决重叠的海洋权利主张是一项技术性工作。根据所涉区域的地质特征,以及所涉申索国和利益相关方的数量,这项任务可能会很困难,但绝非不可能。以中国南海为例,除了中国和台湾,还有五个东南亚的申索国。其中所涉三种争端,通常被认为是一个 “棘手的问题”:
- 关于海洋地貌主权的争端,如西沙群岛(Paracels)和南沙群岛(Spratlys);
- 关于海洋地貌法律地位和权益的争端,比如一个海岸地貌是否应被视为岛屿,或只是一块岩石,或是一处低潮高地,后者无法算作任何独立的海洋区域;
- 关于海洋区域划界的争端。
只要各方都有政治意愿,根据各方优先考虑的利益,找到折中方案,这些争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然而,除了技术问题,还要考虑到各国极力保卫领土主权的倾向、各国之间历史上的不和,以及各自国内利益集团的争斗。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何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南海主要争端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其挑战在于,确保各国能找到一种模式,以避免海洋边界争端转化为公开冲突。
关于边界协议和管理机制的讨论中,专业知识(know-how)是很少提到的因素,但对于东南亚国家如何处理海洋边界来说,这却至关重要。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了解其相邻海域、海洋划界的法律框架,以及相关国家实践的国家,将更可能有效地防止未解决的海洋边界争端演变为公开冲突。当然,要明确的是,专业知识并不足以避免冲突,也不能确保对突出争端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是,东南亚海洋和主权争端管理中的经验至少提供了五个教训,表明专业知识在维护地区的海上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如果一个国家对相关历史记录有很好的了解,并且知道如何论证和陈述其案例,那么这个国家更有可能进入谈判,并可能解决争端。例如,印度尼西亚早期就十分了解海洋边界和划界,这要归功于其成为受国际法认可的群岛国家这一过程中的尝试。印度尼西亚已经与七个海上邻国达成了划界协议,并积极推动谈判。同样,越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与其他东盟成员国(越南1995年加入东盟)进行双边谈判,针对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付出大量努力,从而加强了其实际经验和知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海洋区域划界进展。另一方面,就海洋边界问题,柬埔寨一直倾向于不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该国的相关历史记录在红色高棉联盟(Khmer Rouge)统治时期被摧毁,这也引发了人才外流,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柬埔寨对其现有记录缺乏信心,受过培训的官员数量也不足,长期统治的柬埔寨人民党政府选择推迟谈判,也就推迟了消除未解决争端的可能性。
其次,专业知识可以促使各国加入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这样的国际条约体系。当然,各国可以战略性地决定不加入条约体系,以免影响其各种活动。美国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对非强权国家如东南亚诸国而言,规则的法定化和海洋资源的公平分配相对更有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一般解决机制外,还提供了四种不同的解决机制。即使不使用这些机制,如果政府认为其适用于将来某个时候,那么在那些已经批准公约的国家中,可能会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专业知识为海洋秩序和稳定作出贡献的第三个原因是,可以帮助各国就是否通过第三方解决争端作出有根据的决策。尽管不一定总是使用这种方式(东南亚各国已通过双边谈判有效地划定了海洋区域),确定最合适的方式来解决重叠的海洋权利主张,能够使各国集中努力和资源,以便最有效地划定海洋边界。
第四,当公众对海洋区域及划界的复杂性,即公众专业知识有更好的理解时,可以防止依赖错误信息而非事实的极端立场。这些极端立场常常会迫使政治家采取激进行动。关于海洋边界争端的讨论中,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争端区域内所谓丰富的自然资源。此类主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国间谈判妥协的可能性。此外,这些的问题在于,往往夸大了所谓的财富,而忽视了资源勘探和潜在开发涉及的实际情况:勘探的成本效益比、勘探地质条件可能的复杂性,以及对环境的长期影响和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其他扭曲或错误的观念,与对争端中利害关系的误解有关。例如安巴拉特板块,其位于西里伯斯海的一个海床区域,被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争夺,在21世纪00年代后半期引发了军事和外交危机。安巴拉特板块在印度尼西亚被错误报道为涉及主权问题,而不是主权权利问题。还有人声称安巴拉特将被安全部队“占领”,这种描述是错误的,非但没有促进有利于合作的环境,而且引发了对武装冲突的恐惧。如果社会总体上具备海洋区域、特征和划界的基本专业知识,就更容易说服选民相信和解的好处。
第五,具备海洋边界划界专业知识的国家,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激进行动来强化其主张。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些国家可能更加自信,认为其行动不会开创负面先例,也不会导致冲突升级至无法控制的境地。而专业知识不足的国家,往往倾向于搁置未解决的争端,以避免施加外交或军事压力。例如,具备专业知识的国家,能够更好地评估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与军舰进入被争夺的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的风险。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更了解对手的行动,以减少误解,从而降低反应过度、不稳定和冲突。
总之,来自东南亚海洋边界政治的经验表明,关于海洋划界的培训、教育和国际交流,是对地区海洋秩序的良好投资。对于缺乏获取专业知识机会的国家来说,跨区域伙伴可以提供关键资源,从而增强其谈判技巧和应用国际海洋划界法的能力。
协议、正式机制和区域文化
东南亚今天因所谓的“东盟方式”而闻名,这通常被视为一种模式,一种地区文化或地区象征,体现了东盟成员之间彼此交往的方式。人们认为东盟方式的关键特征是非正式、寻求共识和避免冲突,而非解决争端。然而,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过分强调 “东盟方式” 对东南亚国家如何处理海洋权利主张重叠的影响。
法律手段与东盟所谓对非正式方式的偏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就东盟海洋领域而言,本特刊中的文章证实了东南亚国家依赖国际海洋划界法提供的规则和原则。此外,东南亚国家积极参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会(1973年至1982年,由新加坡的汤米·科主持),从中获益颇丰。所有东盟成员国和东帝汶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柬埔寨是一个例外,柬埔寨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于2019年投票赞成、正式签署该公约。
尽管谈判协议可能更符合本刊中塔瑞希尼·克里希南所称的 “东盟精神” ,但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回避使用诉讼或仲裁等具有约束力的机制,来应对其他区域内外的国家(见斯特拉廷和李-布朗的文章)。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在国际法院处理了有关海洋地貌的主权争端。马来西亚要求海洋法仲裁庭就新加坡在柔佛海峡的填海活动进行判决,菲律宾则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成立的仲裁庭起诉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该仲裁庭由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管理。
可以预测,东南亚国家将继续努力解决未划界的海域争端。这些国家已经认识到确立边界的好处,并利用不同机制解决重叠的海洋权利主张。这些解决争端的尝试与“东盟方式” 表面上并不相容的说法,很可能源于在处理划界问题方面缺乏信心,这可以通过更多的专业知识来解决。最终,“东盟方式” 不应限制东南亚国家采取多种可用的争端解决机制。
本文是拉筹伯大学亚洲研究部、西澳大学国防与安全研究所(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Defence and Security Institute)、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和亚太发展(UNSW Canberra and the Asia-Pacific Development)、外交和国防对话(Diplomacy and Defence Dialogue,简称AP4D)的合作项目“蓝色安全”的一部分。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海事交流、澳大利亚政府或任何合作伙伴国政府的意见。
图片:马来西亚海域的鱼。 来源:威廉·沃比(William Warby)/Flickr。
English version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