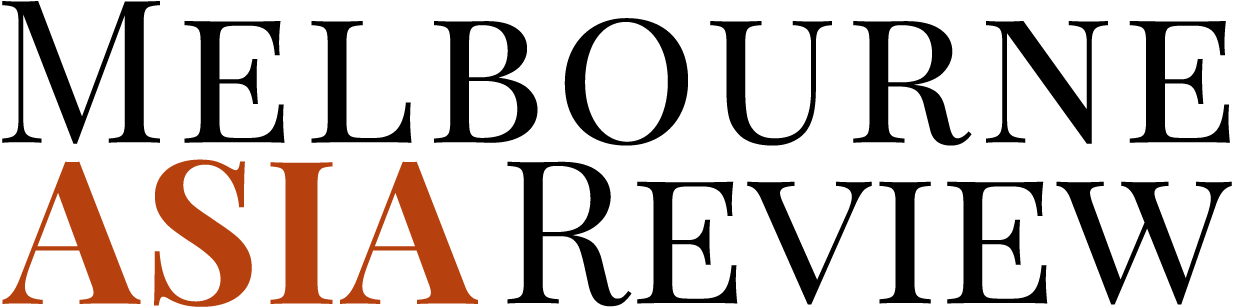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倪欢欢、严茜文、尼克大侠(Nick Tsapakidis)、陈曦
有关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群体(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英文简称 “SOGIE)的事件,一次又一次被媒体、政治家和其他反对人士以夸张、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报道,而且往往是挂上色情的标签。这表明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对SOGIE权利的抵触。
例如,马来西亚一名变性化妆品企业家最近遭受指控,她因触犯《伊斯兰教法》中关于禁止异性装扮的条例而将被定罪。躲过 “过分热心” 警察的大肆搜查以及来自社交媒体的暴力、死亡威胁后,目前她已经逃离该国。 这起案件之后,还发生了一系列其他案件,包括令人震惊的突击检查同性恋场所,以及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第一次高度公开对发生女同性恋性行为的妇女实施鞭刑的场面。即使是东南亚地区相对进步并具有权利意识的国家,如东帝汶–目前唯一被自由之家评定为该地区 “自由 “的国家–也不能指望其将SOGIE权利纳入保护范围。 如果只是为了寻求团结和制定策略,当地相关的活动人士还是应寻求其他论坛为妙。
在此,笔者评估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以下简称“东盟”)对SOGIE权利的支持程度 – 东盟是一个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其有关人权的议程和机制最近才得以一一加强:如为 SOGIE 的宣传提供了一个有帮助的论坛;权衡这些努力所带来的潜在利弊;还有在该地区整体人权都不乐观的前提下,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东盟国家对人权的部分拥护
东盟自 1990 年代以来,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逐步通过的人权议程,极具有创新性,令人惊讶。东盟曾经以一个不干预事物为核心、容忍甚至高度滥用政权的组织,现在已将标准和委员会制度化,并暗中承认了某些权利,正如《东盟人权宣言》所述,“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 。东盟宣称,每个人“都有权不被歧视地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最小程度上对“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加以限制,尽量尊重“地区和国家的不同背景”。经过四十多年不断的结盟和数十年的讨论,东盟人权机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简称 ‘AICHR’)终于在 2009 年成立。测试其权利原有的界限并不仅仅包括2007年《东盟宪章》对 “人权机构 “的承诺,还包括对主要成员国的政治自由化。这显示出,一个多维度的人类安全和发展看似已经扩展至权利的范畴。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性取向权利没有被纳入最终草案。《东盟人权宣言》确实禁止基于 “其他身份 “的歧视,并保护 “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为未被提及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立足点,但包括SOGIE权利将超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目前所主张的权利范围。即便如此,《宣言》仍旧奠定了基础,至少距离SOGIE权利最终被承认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东盟的SOGIE权利倡导:当前状况
东盟各国对任何权利倡导的容忍度在整个地区有所差异,并不是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有活跃的、甚至是公开的SOGIE权利倡导团体。有趣的是,若按照SOGIE的活跃或保护程度对各个成员国进行排名,政治自由度高的成员国反而排名靠后。例如,越南和缅甸(一般被认为是政治自由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最近在组织和认可SOGIE团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新加坡的政治自由化程度很高,但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 (LGBT) 群体却被拒绝合法注册、且其行为被定为犯罪;同样,SOGIE团体在印度尼西亚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敌意。菲律宾虽然可以说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包括骄傲游行、在大学校园里的酷儿学生组织,甚至世界上第一个 LGBT 政党;然而,来自法律层面的保护仍然是不尽人意。无论是在高压政府下的“粉红装饰”(Pinkwashing),还是性取向权利沦为政党牺牲品,SOGIE团体都努力地在声称更民主的国家里打造他们的基地。政治自由化既不是保护 SOGIE 权利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保护 SOGIE 权利的保障。这种不太有利的环境限制了地方组织的发展潜力——即使考虑到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对一些特定权利的主张和倡导(例如,解决与伊斯兰教法的冲突问题而不是应对一般常规法律问题),可能更需要他们将努力集中在国家层面。鉴于很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接受程度和适应的起点不同,这清楚地表明这些西方国家与许多 SOGIE 组织间有所脱节。
值得一提的是,到现在为止,纵使”LGBT “这个词与当地的民风或者对应的原住语格格不入,但却愈发成为整个地区的官方通用术语。 近期在亚洲,至少在地区和国际论坛上,人们开始使用 “SOGIE”(或 “SOGISC”,用 “性特征 sexual characteristics” 代替 “表达 expression”)方面的语言,这有效地质疑了L/G/B/T的分类,使其不再泾渭分明。 也就是说,”SOGIE “将焦点从个人身上(例如,是 “L 女同性恋” 还是 “G 男同性恋”)转移到了一系列特征上,(尽管有些东南亚政治家偶尔会提到一个奇怪的称谓 – “SOGIE人”);因此,这个称谓作为一种身份识别方法可能不太有用,而且在学术界和维权团体之外也鲜为人知。(“酷儿”本身也有类似的作用,它将所有非规范性或性别转变的人都归入其中,尽管这个词有贬义的历史内涵和相对激进的风格。)
对区域性SOGIE权利倡导的研究,最具权威的是一个名为东盟SOGIE核心小组的区域平台,以及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协助力量。 除文莱和老挝等国家外,所有东盟成员国的维权人士在2011年成立了东盟SOGIE核心小组,作为东盟民间社会会议/东盟人民论坛的分支。在此之前一年的东盟人民论坛会议声明首次提出了SOGIE问题;随后的论坛举办了首届LGBTIQ东盟地区会议。这一努力衍生出一系列与LGBT相关的建议,并在结尾的会议声明中呼吁东盟成员国不再间接或直接地把SOGIE视为一种病态或者违法行为,并敦促SOGIE权利成为人权的一部分;使国家政策和实践与2006年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日惹原则》(Yogyakarta Principles,2017年修订并扩展为《日惹原则+10》)相协调;并确保LGBTIQ群体获得平等的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
该核心小组汇集了东盟成员国中与SOGIE有关的一系列民间社会组织,以及一些个人(主要来自一些缺乏相关组织机构的国家)。核心小组由一个区域性的指导委员会和董事会的领导,此外还有一个秘书处设在菲律宾。核心小组呼吁制定包含SOGIE在内的框架和行动方案;对LGBT公民社会进行国内法律保护和授权,以及政府或民间组织与LGBT公民社会的接触;并确保该地区相对民主的国家至少在承认人权和公民自由的范围上取得进展。
即使东盟尚未采纳SOGIE核心小组提交的任何建议,但该核心小组已与东盟人权委员会下属的国家人权机构合作,其中一些机构(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接受纳入SOGIE问题。事实上,自《日惹原则》发布以来,东盟成员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人权机构一直在积极应对与SOGIE有关的歧视问题。例如,2017年,亚太国家人权机构论坛编制了一份最佳指导原则,以便将SOGIE重点纳入人权工作的一部分。不过,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进展不大;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障碍仍然很大。总而言之,尽管东盟SOGIE核心小组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努力改善东盟内部针对SOGIE的指导方针和法律,并向成员国施压,要求其在国内和区域范围内通过和/或维护这些指导方针和法律,但是核心小组这样做的同时也意识到,政策倡导可能是在做无用功。
同时,东盟SOGIE核心小组将LGBT的具体问题与更广泛的政治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希望将SOGIE观点 “主流化”;该核心小组还与整个东盟地区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就成员国的相关问题发表声明。其中包括,关于印度尼西亚刑法的拟议修订及其对性倾向和性别少数群体的影响;关于文莱《伊斯兰教法》中对自愿性行为的惩罚和对身体自主权的限制;以及关于缅甸工作场所对LGBT群体的骚扰。核心小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继续活跃于东盟地区,并与该地区的LGBT组织一起进行需求评估,并且判断疫情对LGBT群体的具体影响以及国家所做出的反应。(这段时期极具挑战性:封城措施对非正规经济和零工经济已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许多LGBT人士在这些经济领域工作;封城迫使LGBT群体与不接受或不尊重他们的家庭成员住在一起;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便意味着各类风险的增加;接触者追踪措施和医疗检查引起了其他的担忧 – 导致性取向曝光并遭受歧视)。 总而言之,核心小组之所以如此活跃,不但为了强调性别和性取向的话题,但也引领了更大的政治运动,并为凝聚跨群体运动提供了机会。
然而,东盟SOGIE核心小组的大部分精力和进程更多地侧重于增强凝聚力上,而非关注政策的制定。
权利倡导区域化的风险与回报
东盟SOGIE维权活动本质上为未来奠定了基础:建立起全面的联络网并整合稳固资源。东盟在此次行动中与其说是诉求对象,不如说是倡导阵地。此概念表明区域机构及其进程创造了组织本身无法控制的战略和话语资源。人权的保护,包括对SOGIE权利的保护,不能仅仅依赖于东盟组织及其有限的贡献。SOGIE核心小组的维权人士既不依赖东盟,也并不仰仗其能在SOGIE权利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他们目的明确地希望LGBT人权被纳入主流思想,并在联盟中有一席之地。
困扰东盟的其实并非法律的条条框框而是社会大众的态度。据悉,一项调查显示,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国民受教育程度高、人口多样国际化,世俗管理远高于其他东南亚临国的国家,61.6%的新加坡民众认为发生于两个成年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当的,18.4%认为多数情况下是不正当的;仅有5.6%的人选择了“毫无问题”。显而易见,这个数字甚至低于LGBT群体本身所占的10%的人口比例。尽管民众的包容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但在18-25岁这个年龄段,甚至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多数情况下否认同性关系的正当性。然而抛开这些数据不谈,新加坡当局已宣布不再执行反鸡奸法(虽然仍坚持将此法载入史册),并且近十年来已然成为了各大企业赞助商每年举办更大规模“一点粉红”性权利活动的首选地,这个说来话长。此外,新加坡的二次独立调查发现有60%的人赞成保留《刑法典》第377A条,即男同性恋间的性行属于系违法行为。当受访者们了解到政府虽然保留该条例,但并不强制执行,更多的民众对该项法条表示支持。这些数据都表明,反鸡奸法的非强制执行已然是世俗在可接受范围内妥协的结果,但不论保留该法律条例会带来怎样的耻辱或固有权利的侵犯,对于同性性行为的“负面”意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揣摩为支持刑事制裁。
东南亚SOGIE权利倡导者们也不可能充分地、随心所欲地进行抗议和宣讲活动,以改变法律或修正社会对LGBT群体的轻蔑态度。他们的维权运动可能同时需要在世俗准则允许范围内进行,但又需要致力于提高世俗准则的上限,同时尝试改革并规避法律约束。堪忧的国内环境成为了东盟SOGIE核心小组地区宣传面临的关键挑战,但也提醒了他们要更多地将重心放在更有表现力、加强凝聚力的目标上,而不是放在实际的政策变化上(虽然这也是核心小组的重要使命),这有助于为运动造势、扩大团队规模,利用规模经济,为战略制定、翻译传播等任务准备,以便于在东南亚国家间或区域内合理分配风险。
前 路
让国际文件涵盖SOGIE权利仍然是很新的想法,例如联合国声明和公约。直到2012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才在2011年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对LGBT人群的性权利保证和国家义务。社会学家和酷儿理论家莫明·拉赫曼 (Momin Rahman)写道,”酷儿权利……最近才成为西方部分地区现代化的合法凭证。即使在前几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意见仍存在很大分歧,以至于无法为确立LGBT权利的声明提供多数支持;尽管时任秘书长潘基文(Bang Ki Moon)曾在2010年公开对此表示支持,但2011-2012年LGBT权利倡导议案由于反对和弃权的票数未能得以通过。
然而,国际舞台正在发生变化。许多政府间和国际组织为SOGIE权利提供了至少暂时性的规范支持,并激发了战略上的创新。联合国本身已采取明确步骤,将对这些权利的关注制度化,于2016年授权一名独立专家,负责防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第一位任职者是泰国国际法和人权法教授(《日惹原则》起草委员会联合主席),维蒂·蒙塔蓬(Vitit Muntarbhorn)。跨国激进主义刺激并塑造了国内环境下的问题出现及问题框架。东盟国家的绝不退让与维权人士直言不讳的坚持之间有着看似不平衡的平衡,这恰恰是人数优势的体现。因为那些面临更大威胁的国家一旦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结盟,便可以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现实情况是,各国的反应从被动到主动或到先发制人;整个社会的反应可能也是如此。活动人士现在可以通过使用 “SOGIE” 作为讨论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人们对 “LGBT” 的反感。而且,特别是在一些不欢迎 “LGBT” 的国家,SOGIE的倡导者可以通过在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不咄咄逼人的国家里代表东盟邻国或者为东盟邻国工作,以此来锤炼自己的技能和战略思维。或许,他们也可能会非常不屑地给那些所谓的 “恐同精英” 们提供来自于东南亚的学说和理论,以证明他们的所主张的观点是本土的、恰当的。
LGBT人权包括什么,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东盟SOGIE核心小组等机构)如何在这一范畴内构建和促进,都需要澄清。从短期至中期来看,人们可能会把东盟SOGIE核心小组视为构思和发起运动的一个空间–仅用来定义和追求思想表达与情感宣泄的目标,从而忽略了在成员国内部取得政策性成就的机会和局限。这些目标可能会响应和扩大以规范为导向的地方性运动,这些运动更注重 “LGBT尊严、自尊和公平待遇” ,而不仅仅是权利本身,但是仍需要加大力度在区域范围内进行推广。鉴于这种规模,虽然东盟SOGIE核心小组确实与成员国的民间社会组织(核心小组积极分子也往往参与其中)一起计划了集体行动,但是在个人或社区层面赋权的具体实施仍然需要地方级、国家级组织做更多努力。
至于东盟 —— 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和《东盟人权宣言》—— 似乎也没有期待对 SOGIE 权利的保护能从正式意义上产生巨大转变,鉴于东盟地区的法律和主权结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东盟所拥有机制的权利都是有限的。东盟人权的各项事实可以说是搭建了一个提供讨论和团结各方的平台。然而,东盟的制度和进程创造了东盟本身无法预料的机遇——使东盟的架构走向合法化,这可能与其创始人和当今领导人的意图大相径庭。正如政治学家凯伦·紫薇(Karen Zivi)所说,
“主张权利的民主潜能不一定存在于由它所产生的法律或政策中,也不一定来自于终结某一特定的政治辩论中,而是在于它可以使因疾病、阶级、种族和其他因素(在本文中是指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沉默的人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参与到改变民主共同体本身意义的民主公民行动中来。”
这些 SOGIE 权利主张不仅仅是在东盟共同体中争取一个诉求空间,它们的行为更可能成为“仪式和标志”这种表象混合体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专家马修·戴维斯(Matthew Davies)认为,“东盟在没有其他联盟成员参与的情况下为外界创造出一个团结一致的感觉”。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东盟SOGIE核心小组本身已经积累了知名度、认可度和各种联盟关系 —— 这种坚持不懈进行对外联系、宣传、发展自身能力和提高知名度的努力都会被记录下来。但在此过程中,将这些格外被忽略的权利摆在桌面上并逼迫东盟取消这些权利,这等于间接承认并切证实了提出这些主张的社团:所以当东盟需要做出是接受还是拒绝的确切回应时,不应忽视、甚至是无视这些主张者。
东盟是否能够认真对待其对人权的承诺,或者它所承认的权利名单是否具有包容性,目前看来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会员国之间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差异,以及社会层面上的而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对同性恋的恐惧,都像是在劝告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过分重视一些本应是合法的权利。如果说东盟自视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SOGIE权利的机构,那么在维权人士致力于社群建设并奋力使其复杂的、充满挑战的性别组合得以认可的同时,东盟所做的具体工作可以说是为这些维权人士在现有的框架和政策中指引了方向。这里的重点是不要把东盟看作是一系列需要被游说的机构,而是要看到东盟为建立团结统一的地方维权运动所提供的空间和资源;东盟在这个权利倡导的故事中变得更像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非主角,至少目前公众的感觉是这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虽然东盟 SOGIE 核心小组在这一过程中的努力充分体现东盟所主张的那种“以人为本”的重点和区域认同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区域共同体中,东盟作为一个完整主体却选择不去保护且不予承认SOGIE 权利。
本文借鉴了对东南亚维权人士的采访,并改编自2021年3月发表在《亚洲研究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图片。骄傲游行和节日庆祝,马尼拉,2019年。资料来源: Metro Manila Pr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