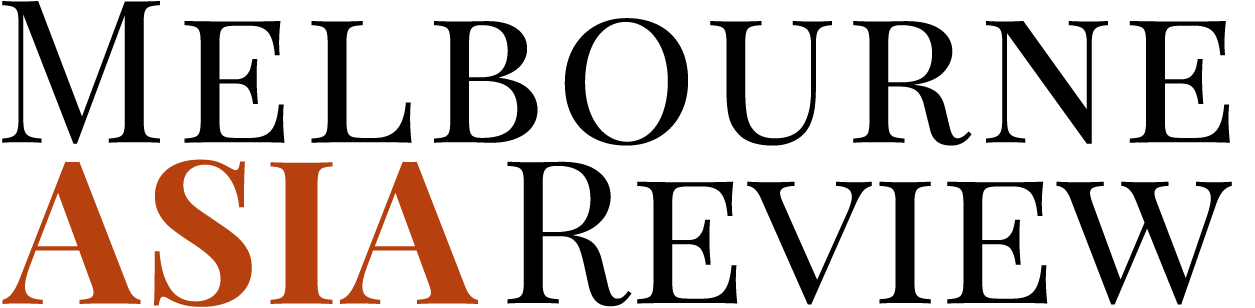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何嘉懿 闫华泽 刘舒悦 周利霞 裴一霖 马铭阳
在2010年初的某天,我去逛了逛大马士革霍尔布尼(al-Halbouni)区我最喜欢的书店。霍尔布尼是阿拉伯书友的天堂:这里有几十家书店紧挨着,摆满了各种流派和类型的书籍。我仔细浏览着面前的书架时,突然发现了有一本书脊是空白的,这显然表明它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印刷的稀有文本的摹本。我的直觉很准:我偶然发现了一本没读过的古典阿拉伯哲学著作的评注。但是当我的目光顺着书页往下看时,我的兴奋很快被惊讶所取代。我停下来盯着那两行西里尔文字,旁边的阿拉伯文字解释道,这本书是1901年在喀山(时属俄罗斯帝国)印刷的。我以前在莱比锡、勒克瑙,抑或是位于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许多地方都看见过印刷文本,但这本书让我浮想联翩。我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球,一个尚未被探索的新世界——这引发了一个问题:阿拉伯语研究的教学是否过于狭隘?
重构澳大利亚的阿拉伯语研究
现今,阿拉伯语通常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语言和伊斯兰教的礼仪语言。但阿拉伯语及其文学遗产远远不止是一种民族或宗教语言:它是一门经典的世界性语言,传递出的文化跨越千年依然充满活力。作为一种语言,它可以为人们打开文学、文化和哲学知识的宝库。从南京到里斯本,从喀山到开普敦,从马尼拉到爱丁堡,阿拉伯语及其思维模式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界。阿拉伯语在地理上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不同亚洲文化的复杂互动,使我们需要换一种角度思考阿拉伯语研究。如果想厘清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的一些互动和联系,就需要对非洲-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进行跨学科和跨国的研究。
接下来,我将追溯阿拉伯语在亚洲传播路径。我可以为非洲和欧洲分别撰写类似的或更长的文章。虽然阿拉伯语的每一次传播路径都可以作为长期研究的基础,但我的重点在于阐释其传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阿拉伯语已然并将继续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 而阿拉伯文化奠定了东南亚和南亚文化大部分的基础。我们应该重新设计阿拉伯和亚洲研究课程,以便让年轻的学生更好地接受这一文化领域。
阿拉伯语的起源
早在两千年前,阿拉伯语就已经成为阿拉伯半岛北部居民的语言。阿拉伯人当时政治地位式微 ,因此人们对他们的语言不太感兴趣。一些阿拉伯人安于定居,另一些半逐水游牧。汉志位处红海沿岸的西部地区,处于印度(途经也门)与大马士革之间的古老的贸易路线上。阿拉伯人以诗歌为荣。他们以诗寄情,诗中彰显爱与背叛的主题,号召部落团结武装,抑或针砭讽刺敌人。
伊斯兰教永远地改变了阿拉伯语的命运,阿拉伯语从民族语言变成了宗教和许多帝国的语言。公元610年,在汉志贸易路线上的阿拉伯中心——麦加城,先知穆罕默德开始接受真主的启示,带来了为后人所熟知的《古兰经》。《古兰经》启示人们避免邪神崇拜,坚持一神论,相信穆罕默德是真主派来指导人类的最后一位先知。《古兰经》被认为是真主的原话,而这种宗教影响力正是阿拉伯语力量的历史基础。
阿拉伯语的早期扩张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事件后,阿拉伯语将不会再局限于经文的仪式化语言。阿拉伯语崛起的历程中有三个重要的节点,它们主要发生在八世纪,分别是:阿拉伯语语法的明确和其拼字法的改进,阿拉伯语作为帝国语言的使用以及造纸新技术的诞生。
阿拉伯语语法发展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阿拉伯语消亡的忧虑。在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多语言社会中。所有的语言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与新语言的接触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先知的同伴们察觉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开始共同努力,保存《古兰经》习语中的阿拉伯语风格。阿拉伯人的诗歌被记录下来,并经由母语者,代代相传。在活跃的学术界中,有关诗歌的真实性和其规则的形成方法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语言学工作在西伯韦(Sibawayh,卒于约公元796年)的语法专著《奇迹之书(al-Kitab)》(字面意思为“书”)中达到了顶峰。《奇迹之书》是对阿拉伯语语法的完整解释,附有大量引注。在保护阿拉伯语的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古兰经,穆斯林们开始仔细研究阿拉伯语的语法机制。更具体地说,《古兰经》曾多次公开向阿拉伯人这个满是诗人的民族发出创作挑战,从而吸引了人们对经文中阿拉伯语的关注,以使人们正视《古兰经》中无与伦比的修辞。看似矛盾,但为了理解《古兰经》的不可模仿性,学者们在阿拉伯语语法、修辞学和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些著作至今仍在传诵和欣赏,对世界历史、语言学和伊斯兰法学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期间,阿拉伯文字经历了一系列微小但重要的变化。譬如,同一个字母的不同发音通过点来区分,使用小符号来清晰表达短元音,并标准化拼写。
第二个发展跟阿拉伯语的政治意义有关。倭玛亚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Abd al-Malik ibn Marwan,卒于公元705年)颁布法令,阿拉伯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取代其他行政语言(即彼时拜占庭帝国通用的希腊语和萨珊王朝的中古波斯语)。在官僚机构中使用阿拉伯语意味着许多抄写员必须接受培训,他们抄写手册的风格与现在的写作手册极为相似。阿拉伯语也变得随处可见:无论硬币上还是建筑物的纹饰,皆可见阿拉伯语的踪影。
第三次发展得益于穆斯林引进中国造纸术,这一发展为阿拉伯语的传播奠定基础。在此之前,穆斯林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纸莎草纸或者羊皮纸。纸莎草纸是通过捣碎纸莎草的茎制作而成,虽然制作成本低,但不耐用。羊皮纸是由特制的动物皮制成,虽然耐用,但是成本昂贵。而当时纸张是用棉花或者亚麻布(不是木材)制作而成,它不仅耐用,成本也不高。
到了9世纪初,阿拉伯语已经具备了广泛使用的条件:它的语法有充分的文献记载,方便人们学习;它成为了当时帝国的官方语言,并得到了一群资助者的支持;它可以通过相对廉价的纸张传播。穆斯林去到哪儿,就会带着手稿和文学经典把阿拉伯语传到哪儿。阿拉伯语从此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它环绕地中海,穿越丝绸之路,贯穿印度洋,横越沙哈拉沙漠。
阿拉伯地区中的阿拉伯语
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时,只有阿拉伯半岛北部和叙利亚沙漠地区使用阿拉伯语。到8世纪中叶,伊斯兰帝国已经从伊比利亚半岛(在现西班牙)扩张到了信德(在现巴基斯坦)。虽然伊斯兰教是统治阶级的宗教信仰,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但是人们并没有马上接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几个世纪后,阿拉伯语才成为了阿拉伯南部、黎凡特、埃及和北非的主要语言。在今天看来,这些地区正是属于阿拉伯地区。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出现也并不一致,农村地区阿拉伯化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毫无疑问,对任何穆斯林来说,阿拉伯语的吸引力是必然的:因为当时阿拉伯语是唯一能够确保精神和物质利益的语言。
在这个地区,不同的语言有着不一样的命运。阿拉伯语逐渐取代了古叙利亚语(一种阿拉姆语)的地位。在穆斯林来到黎凡特之前,古叙利亚语曾是主要的语言。叙利亚、伊拉克乡村偏远地区的人和这些群体的散居人口仍在使用和古叙利亚语相关的语言(被称为新阿拉姆语)。很多东正教教徒也还在说古叙利亚语。虽然库尔德语和波斯语地区临近阿拉伯半岛,但是阿拉伯语一直没有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语言。但是阿拉伯语确实在整个北非,甚至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了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阿拉伯语传到该地区之前,还是现在,也门和阿曼之间的地区仍在使用几种南阿拉伯语言。阿拉伯人的移居、当地人对非阿拉伯语言缺少支持,和对征服者语言的态度等因素都影响了阿拉伯化阿拉伯化的进程。
在9世纪和10世纪,许多穆斯林(主要是波斯人)参与了舒欧比亚运动,抗议阿拉伯人在穆斯林社会中的特权地位。阿拉伯人显赫的政治权力使得阿拉伯语的地位特殊。在阿拉伯语为政治权力提供特权的社会中,阿拉伯人必然会拥有不平等的权力。舒欧比亚运动抗议者的立场很微妙:当阿拉伯语被视为宗教优越性和政治霸权,遭到了抵制,但阿拉伯语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科学语言却,受到欢迎。吊诡的是,舒欧比亚运动成为了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文化传播得更广、更深的必然因素之一。这一点我将在后文加以详述。
阿拉伯文学文化
九世纪之前,大多数用阿拉伯语书写的人,都不是阿拉伯族裔。阿拉伯语成为了世界文化的新站点。聂斯托利教派的基督徒把希腊式学习法翻译成阿拉伯语(大多数通过叙利亚语翻译):雅典伟大的哲学家们(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及亚历山大的学问:盖伦的医学、欧几里得的数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波斯人带来了他们的中古波斯语学习法,其中常常包含梵文知识。《卡里来与笛木乃》是早期伟大的阿拉伯散文作品之一,是由Ibn al-Muqaffa(卒于公元759年)从中古波斯语翻译而成,发轫于梵文书《Panchatantra》(“五卷书”),后者是一本教授美德的动物寓言书。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用希腊语、科普特语、吉兹语、波斯语、梵文以及很多其它语言写的文化和科学知识都融入了阿拉伯语,使之成为一门真正世界性的语言,遑论当阿拉伯语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后写的大量宗教文献了。
每个族群和宗教团体都和阿拉伯语有着独特的渊源。比如,叙利亚的基督徒在被他们称为加许尼文的叙利亚语手稿里写阿拉伯语,犹太人在希伯来语手稿里书写阿拉伯语,现今被称为犹太-阿拉伯语。现今任何说阿拉伯语的人如果花几个小时理解了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的字母在阿拉伯语中的使用,那么他们都可以读懂这些文字。阿拉伯语是文化和语言的熔炉。它是每个人都想理解的语言,每位说阿拉伯语的人也都渴望被理解。
波斯语:一个采用和改编阿拉伯语的典型
十世纪为波斯语言引领了一场新的文学复兴。在七世纪伊斯兰征服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语作为文学语言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定都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名义上统治了整个帝国,但到九世纪时,各种地区本质上都变成了自治区,实质政权落入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手中。在伊朗西部的一些酋长国除了大量资助阿拉伯语的科学和文学之外,还开始资助波斯语的文学创作。在国际化的环境中,波斯文学界创造了一门鉴赏性的语言:新波斯语。新波斯语是阿拉伯语词汇和成语大量注入各种中古波斯语言后的混合物。新波斯语采用了阿拉伯语的字母系统,修改了几个字母来适应阿拉伯语中没有的音,创造出新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两种语言在十世纪的这些波斯王朝里各司其职:阿拉伯语主要用于科学和宗教目的,波斯语是法庭语言和文学的主要语言。这种新的文化模型深受萨曼尼德帝国支持,帝国的中心在撒马尔罕,后来在布哈拉。
采用和改编阿拉伯语成语、图案、词汇和字母系统的波斯语模型,具有分水岭意义。首先,它为其它语言提供了一个模型,将阿拉伯的语言、文学和字母系统(比如普什图语、维吾尔语、突厥语、乌尔都语以及很多其它语言)地方化。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波斯语模型成为了一个棱镜,其余的亚洲大陆透过这个棱镜了解阿拉伯语。这个混合的阿拉伯-波斯文化成为了后来波斯化世界的基础。相比阿拉伯语在非洲和南欧的传播,这个混合文化是阿拉伯文化在亚洲大陆传播的决定性特征。
中亚和突厥–蒙古地区
在文化形态建立初期,萨曼尼德帝国抓住时机,将中亚的土耳其人带至伊斯兰。十世纪末,突厥加兹纳维德人颠覆了萨曼政权。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萨曼帝国发动了第二次社会-政治进攻,持续了千年之久。突厥-蒙古人民在中亚穆斯林中成为主要政治力量。他们的军事实力捍卫了他们的政权,也保护了他们所遇到的阿拉伯-波斯文化。
20世纪之前,在亚洲的某些地方,突厥语用于军事和行政事务,由此产生了一种三方语言模型。现如今,虽然我们将过去的突厥语与如今的联系起来,但各族系的突厥人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源于中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突厥语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拉伯和波斯语的影响。之后更迭的突厥和蒙古政权,将阿拉伯-波斯文化从东欧传至中国和韩国。
一些比较有名的帝国,包括塞尔柱帝国(11世纪-12世纪)、奥斯曼帝国(14世纪-20世纪)、伊儿汗国(13世纪-14世纪)和帖木儿王朝(14世纪-16世纪)。公元10世纪,伊斯兰文化从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河上游传至伏尔加鞑靼地区,这也是另一个文化传播的例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喀山成为出版业的重镇,这里出版所用的语言主要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彰显出三方模式(这三种语言三足鼎立局面)的源远流长。
对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探讨有三层含义。首先,无论波斯人去到哪里,阿拉伯语都用于科学和宗教领域。在现在亚洲的很多地方,由于阿拉伯语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通用语言,所以阿拉伯语是唯一的存在。第二,由于几乎所有使用波斯语的作者都懂阿拉伯语,并且波斯语中充满了阿拉伯文字和思想的烙印,因此波斯语可谓深受阿拉伯语的文化影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将阿拉伯语研究限于阿拉伯的地区或文本。我们深入研究了习语在经典文学中的运用以及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这推进了文化的多元化。这种文化的混合和交融是阿拉伯语在亚洲地区的流动的主要原因。
南亚
从11世纪开始,如今的巴基斯坦语和南印度的地区就受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混合受到了莫卧儿帝国的影响,彼时土耳其人接受了波斯文化,并从16世纪开始统治了该地区。19世纪之前,波斯语一直都是宫廷用语。
虽然从16世纪开始,乌尔都语兴起,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印度著名学者理查德· 伊顿(Richard M. Eaton)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波斯时代的印度:1000-1765年》讨论了这些敏感的话题。在莫卧儿帝国时期,阿拉伯语仍然用于科学和宗教。
19世纪,印度印刷了很多阿拉伯和波斯文本。在加尔各答、勒克瑙、德里和其他一些地方展示了这些语言所具有的活力和通用性。在南印度,用波斯-阿拉伯语书写,混有阿拉伯外来语。关于阿卫语,它是泰米尔语的方言,用波斯-阿拉伯语写成,并且带有阿拉伯的外来语。阿卫语在印度的南端和斯里兰卡广泛使用,用于书写一些诗歌、文学及宗教用语。
中国
在第八世纪,大量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开始在中国定居。中国元朝时期(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蒙古人偏向穆斯林,许多中亚地区的学者便进入阿拉伯和波斯,寻求进入中国宫廷之道。十四世纪时,中国的穆斯林群体发明了一种用阿拉伯文字书写汉语的系统,取名为“小儿经”并沿用至今。为了了解一系列的古典文学,传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还学习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汉克塔布》(《Han Kitab》)是伊斯兰历史上最震撼的知识与文学巨作之一。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合:“汉克”是汉语单词“中文”之意,而“塔布”则是阿拉伯语单词“图书”之意。在十七世纪的清朝,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的王岱舆在掌握伊斯兰教义后,钻研儒学、佛教和道教,并开始创作《汉克塔布》。他选择用中文,而不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这使他的作品极具中国特色。
东南亚
在南亚人与也门人接触后,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东南亚。不像亚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相连,波斯人的文化在东南亚并不普遍。马来语最早出自爪夷文,爪夷文现存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1303年的丁加奴铭石。爪夷文也曾用于编写许多东南亚的许多语言,包括菲律宾的陶苏格语。此外,爪哇族、马都拉族及巽他族的语言也时而使用阿拉伯文字系统(被称为Pego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在她的《伊斯兰翻译:文学、皈依与位于南亚与东南亚的阿拉伯大城市》中,深入发掘了这个世界。
全球阿拉伯研究
我在大马士革发现了一本于喀山印刷的阿拉伯语书籍,这促使我再度对阿拉伯语开展研究。在非洲、欧洲和亚洲的作用以及波斯语在整个亚洲的影响中,阿拉伯语都至关重要,但对于更广泛的学术界却鲜有人知。阿拉伯语不仅是一颗星星,更像一个星座。虽然现代民族国家和国家边界可能让人忽略了阿拉伯语的广泛影响力,但我们也忽略了跨文化的不利影响。
如果将这一点考虑在内,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澳大利亚的阿拉伯语研究,将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阿拉伯地区,而是扩大和充斥到亚洲对于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化、手迹和文学的影响。这样,阿拉伯语研究就可以真正实现跨越国境,由此追溯至不同地域阿拉伯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以及与其他文学文化的动态交流,例如波斯语、梵语和汉语。
这些文化的变化、交融和分歧对如今亚洲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使得我们从各个角度研究阿拉伯语,不是偏重一隅,而是将融合与互动并重在首要位置。通过研究丝绸之路以及印度洋的贸易路线,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同样的,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亚洲的阿拉伯文字、或受阿拉伯语影响的文字,也是一个有趣且生动的过程。以这种方式在大学中教授阿拉伯语的研究,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课程更加生动。甚至可以当我们在超国家主义与超全球化之间摇摆、迷失和思考时,帮助我们找回自我。
Image credit: pxfu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