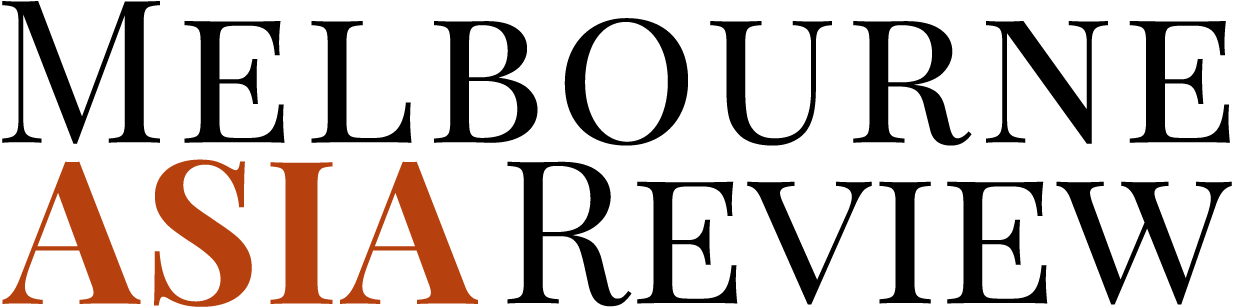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孙婧、谈佳蕙、王柯然、邢晓书、杨柳依、张小言
一个红绿灯会对另一个红绿灯说什么?“别看,我在变。”眨眼间就会错过这种改变。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澳大利亚电视剧的变迁。莱斯利安·霍桑教授(Lesleyanne Hawthorne)将这一流派命名为“现代版寓言剧”,它“隐性或显性地”传达了有关“澳大利亚社会性质,例如对种族多样性的接受程度”的讯息。
谈及最能代表澳大利亚的电视连续剧,大多数人很可能会提到《聚散离合》(Home and Away),这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流行文化出口产品〔仅次于先前一部电视剧《邻居》(Neighbours)〕,《聚散离合》出口至80余个国家,目前在九频道播出。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夏日湾”的虚构小镇,这片土地永远充满阳光,没有任何丛林山火。小镇远离喧嚣,与悉尼和墨尔本这样充满异国风情的首府城市距离甚远,这就是为什么小镇没有 “意大利披萨店、中国餐馆,希腊或黎巴嫩牛奶吧”。 《聚散离合》于1988年开播,该剧是“大规模移民前、主要由盎格鲁人居住的澳大利亚”社区的缩影,剧中皆是“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寄养儿童,“在语言、文化和个人风格方面完全澳洲化,因此被认为是纯正的澳大利亚人”。近三十年后的2015年,作家本杰明·罗(Benjamin Law)〔代表作《罗家趣事》(The Family Law)和《与龙共舞》(Waltzing the Dragon)〕,在《月刊》中一篇题为《亚洲人崛起》的文章中写道,“截至1990年,亚洲人约占新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截至 2010年,“超过1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有亚洲血统。 但在这个殖民地定居者国家的文化想象力和媒体视野中,主演皆为白人演员的现象仍很普遍”。
迈克尔·韦斯利(Michael Wesley)教授在其书《邻国:澳大利亚和崛起的亚洲》中提到1990年至2010年这段跨千禧年的时期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富有、开放和日益安全的二十年”。同时澳大利亚人也矛盾地观察到国民“自满于自己的国家与世界的联系,对世界如何变化如此无知,对这一切带来的影响毫无准备”。十年后的今天,在与澳大利亚利害相关的广阔世界里,这种令人困惑的兴趣缺失导致, 在主流媒体和艺术领域里对亚裔澳大利亚人的描述很少。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说澳大利亚的电台、画廊、电视或剧院行业中没有亚裔澳大利亚人的身影;而是说,在一个高度互联、全球文化材料充斥的时代,对本土的澳大利亚亚裔文化内容和人才的忽视显得尤为严重。这种忽视的根源也许是因为澳大利亚长久以来的民族文化自卑感(cultural cringe),但如果在亚洲——不断地、肯定地、可预见地——即将来到或已经生活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这种自卑感,那这种漠视会引发人们关注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自我定位。
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人的想象中,巴厘岛是寻常的消费旅游好去处、是澳大利亚的后花园;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流行文化中所描述的亚裔在澳定居的丰富历史,对除了竭力且坚定寻求之人以外的所有人来说仍然是模糊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亚裔澳大利亚人的故事不断出现在澳洲媒体的视域中,这些故事中,尤其是涉及澳洲人初踏这片尚未拓荒的原住民土地历史的故事,为白人定居者的霸权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警告和纠正。正如参议员黄英贤(Penny Wong)在《混血国》(Mongrel Nation)中对前种族歧视专员蒂姆·索特波玛玛森(Tim Soutphommasane)所言:
首先要认识到,亚洲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身份。因此我认为,在自我身份塑造上如果我们仅将自己视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前哨所,那么在参与亚洲地区事务时澳大利亚总是会遇到麻烦,不是吗?
在过去的十年里,亚洲对澳大利亚的影响随处可见,从入境移民(留学生、临时技术工人、经济移民)到出口产品市场(澳大利亚的煤炭、农产品和水产品、文化产品)。至少在我们群体(即亚裔澳大利亚人)的想象中,亚裔澳大利亚人的故事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但它在约定俗成的“白人”为主流和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批判的,都很少被接纳。
对“亚对澳影响力”的出现,这样一种“获准性无视”的疏忽反应,对“澳对亚影响力”有直接和长远的影响。曾经,亚洲研究是提升澳大利亚国民亚洲文化素养的首选学术手段,曾通过“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鼓励国民学习有关亚洲国家文化语言、社会、民族和世界观的深厚专业知识。矛盾的是,这种做法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把亚洲明确地置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力边界之外,而其他的则置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力边界之中,即使该国(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区域内日益团结。它掩盖了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至少在25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来往和联系,当时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家来到澳大利亚并在此站稳脚步。在“新科伦坡计划”(New Colombo Plan)下,重点仍然是外部化的:把澳大利亚人派到亚洲去,虽然这或许是澳大利亚认识亚洲新面貌的必要前提,但却牺牲了澳大利亚本土亚裔澳大利亚的传承。当今时代之中所体现的高度机动化特性,被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hmunt Baumann)称为流动现代性。即便新冠疫情来袭,现如今亚澳两洲之间的“他者化”裂痕早已不复存在。迥异的个体、地域和风情藉由日新月异的出行方式(撇开新冠疫情不谈)、跨国移民全新趋势、技术支持媒体内容在不同时区同时发布,允许用户参与多情境多语言的流行文化而联系到一起,例如,人们通过诸如谷歌(Google)翻译和油管(YouTube)的全球化同步文化平台,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在家中轻松享受韩国流行音乐(K-pop)或宝莱坞(Bollywood)带来的乐趣。
此先的研究关注了在澳大利亚的政策和管理事务中坚持亚洲素养,以及亚洲素养在澳大利亚的政策和管理事务中发挥的影响。诚如这些学者所言,政府以往提供的绝大多数经济条例旨在让澳大利亚人能够“应对”亚洲影响〔例如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这是澳大利亚人“需要”亚洲素养的一个主要原因。澳大利亚将自己想作该地区(北及亚洲,西至印太)一枚摇摆不定又自相矛盾的转轴,身陷一场关乎亚洲本身“概念”的严苛谈判之中——随着二战后地缘政治突出和重组,亚洲俨然成为“我们时代的地区”之一。显然,澳大利亚人只能采用“亚洲-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亚洲”双向交织的方法来导向亚洲素养影响。亚洲素养作为一项技能,只能通过语言和文化,而不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获得。正如同土著人群体一再强调的那样,土著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由讲故事的方式揭示。但当谈及生活在澳洲其他的“另类”群体,诸如非英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移民定居者和二十一世纪的亚裔来说,他们使用基于种族的非英语语言模式,譬如NESB(非英语背景)、LOTE(英语以外的语言)、CALD(文化与语言多样化)等。
如此一来,亚裔澳大利亚人既是维系澳大利亚与北方大陆——那片殖民意义上被称作“亚洲”的大陆——的纽带,又是不同于“亚洲式”邻国的独立群体,亚裔澳大利亚人虽与亚洲人同根同源,却不能认为两个群体共享完全相同的语言或社会政治习俗。从这个角度来说,亚裔澳洲人是澳大利亚通往亚洲的桥梁这一命题既是也非,许多亚洲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容易出现一个严重误区:亚裔澳大利亚人与亚洲人经常被划上等号,并被认作通往亚洲的渠道、亚洲产品的消费者。虽然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并不是亚裔澳大利亚人身上唯一的特性。事实上,正如墨尔本的中澳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马克·王(Mark Wang)所说,我们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历史,我们谈的不是中国历史。然而,在诸如由新冠疫情造成的种族问题上,将亚洲人和亚裔澳大利亚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显得尤为不妥。
发声的重担落在亚裔澳大利亚人身上:他们即要证明自己亚裔感情的合理性,又要保持他们作为正儿八经的澳大利亚人所享有的合法权利。面对盎格鲁人和凯尔特人作为澳大利亚国民的主体的现实,亚裔澳大利亚人有责任去追寻和记述早期亚洲人迁移至澳大利的事实,这些史实不可磨灭却尚未记入史册,它能够证明亚裔无疑与白人定居者一样属于这片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更需着重注意亚裔澳大利亚人在媒介和流行文化中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讲述当代澳大利亚的故事,并说服全世界,澳大利亚与其多元文化的称呼匹配。我们的亚洲特性并不仅仅像《厨艺大师》中一些被熟知的,能带来新奇味觉的食物那样奇异,或者在充斥着平等和对立的亚裔妖魔化中,这一特性使亚裔成为新冠疫情来袭时人们怀疑和指责的对象。这时,流行文化可以成为理解亚裔澳大利亚人经历和身份的重要辅助手段,使我们能够完整叙述带有殖民特征的各种定居点。
过去的五年中,澳大利亚公共领域针对亚裔澳洲人在澳大利亚电视屏幕上缺乏代表性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此类讨论受到以下报告影响,比如《审视我们自己:澳大利亚电视剧的多样性反思》和《改变平衡:澳大利亚艺术,电影和创意领域的领导力中的文化多样性》。大多澳大利亚电视节目观众都不知道,如今在网飞(Netflix)、亚马逊(Amazon)、家庭影院频道新版(HBO Now)和 iTunes 等诸多平台上,电视节目逐渐开始展现多样性,例如《校长》(The Principal)、《未上市》(The Unlisted)、《狩猎》(The Hunting),甚至是饱受批评的《哈比人来了》(Here Come The Habibs)。2020年,体现多元文化元素融合的新剧《饥饿的鬼魂》(Hungry Ghosts) 爆火,这是一部共四集的超自然电视剧,该剧讲述了越南战争带来的创伤。该剧的演员阵容为30多名亚裔澳大利亚演员和325名亚裔澳大利亚临时演员,这在澳剧中实属首例。持续火爆的澳洲真人秀《厨艺大师》中,主持人梅丽莎·梁(Melissa Leong)身上代表了两个层面的多样性:女性和亚裔。关于种族及多样性的讨论主导了该节目的评论。2021年的《回味》(Aftertaste)保准更加有趣,在这部六集喜剧中,世界闻名的“暴躁白人”主厨在无奈之下回到澳大利亚的小镇,开启了人生新篇章。而当地已经有了一家明星餐厅,经营者是一位颇具创新精神的年轻亚裔,他曾在这位名厨手底下做学徒时遭受过种族歧视。
然而,电视剧特殊的是,它通常不像其他媒体形式一样具有艺术合法性,也因此电视剧是凭借贴近老百姓生活和引起他们共鸣而进入到大众话语。凭借着广泛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反智偏见——认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经常受到抨击——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电视剧在改变带有偏见、根深蒂固的白人主导叙事角度(视其他民族皆为外来者)上能发挥非同一般的力量。接着谈《海茨邻里故事》(The Heights)。作为澳洲原创瑰宝,《海茨邻里故事》恰逢其时地改变澳大利亚在电视剧《聚散离合》中消费全世界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当代澳大利亚在亚洲邻国眼中的真实模样。至少在剧中的城市环境中,这样的呈现或许是多元文化多样性时代到来的宣告和崭新标志。重要的是,与存在已久的多样性标签竞争者《聚散离合》和《邻居》有所不同,人们在肥皂剧这一流派中最大化地呈现了多样性。《海茨邻里故事》已经在英国播出,但显而易见的是,该剧需要在我们的亚洲邻居中进行宣传。该剧的制作公司是火柴盒影业(Matchbox Pictures)——由托尼·艾尔斯(Tony Ayers;出生于葡属澳门的澳大利亚籍创作和制片人)等人合作组建的实力派影视公司,该剧的创作者是沃伦·克拉克(Warren Clarke)和刘桂明(Que Minh Luu;网飞澳大利亚本土原创导演,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执行制片人)。这部电视剧新秀体现“亚洲世纪”中澳大利亚与亚洲地区的关系。该剧于2019年首播,随后的第二季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播出,但是否已经续订第三季尚不清楚。
该剧以阿卡狄亚海茨(Arcadia Heights)贫民区为背景,其多样性不言而喻,该剧情节自然且切合实际,六个家庭的故事构成了主要的情节,根据剧情主线配角在各家庭间交叉穿梭。该剧在珀斯拍摄,而不是在墨尔本、悉尼,有相当一部分剧情取景于当地一家名为铁路(The Railway)的酒吧和名为同香食品公司(Dông Hu’o’ng)的街角越南杂货店。剧中这两处场所均由雷厉风行的女士经营。沉着冷静的黑泽尔·墨菲(Hazel Murphy)由经验丰富的女演员菲奥娜·普雷斯(Fiona Press)饰演,她有着37年的演艺经历,而艾瑞斯·德兰(Iris Tran)由刚刚出道的难民拥护者卡瑞娜·黄(Carina Hoang)扮演。她的家人于1976年乘船逃离越南,并住在印度尼西亚的高良难民营。
长期以来,酒吧都是肥皂剧的典型拍摄场景。自1960年起, 英国加冕街已经录制了超过10,250集,通过当地酒吧的不同策略展示了英国不断变化的社会风貌。在《海茨邻里故事》中,街角的越南杂货店也发挥了同等的作用 。实际上,该剧取实景地于37年前建在北桥上的同香食品公司,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城市空间随着迁徙发生的改变。
《海茨邻里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被贵族社区所包围的公租房托尔斯公寓(The Tower)中,尽管价值观不同,但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甚至突破内心的障碍找到了真爱。墨菲一家(the Murphys)和戴维斯一家(the Davies)切身演绎了不健全家庭的样子;而德兰一家(the Trans)和贾法里一家(the Jafaris)则展现了一种难民精神的凝聚力,与其他一些爱恶作剧的邻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人及亚洲人后裔的居民受到原住民长老麦克斯叔叔(Uncle Max)、帕姆姨妈(Aunty Pam)以及米奇(Mich)和莱妮(Leonie)等原住民核心人物的指导。在这个虚拟社区中,所有居民间的紧张关系都被难以置信的亲密共存所冲淡,这种共存既真实又令人向往。这部剧试图把所有的“问题”,诸如原住民、种族、残疾和阶级都穿插在同一个故事背景中讨论,并设法凸显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差异、少数民族社区中的同性恋、当地政客的政治把戏、赌瘾和毒瘾的陷阱、青少年性教育等问题,当然还有肥皂剧中必不可少的大量床戏。在所有这些主题中,该剧叙事并没有动摇其展示多样性的初衷。无疑,澳大利亚观众应该能从这部在沿海城市上演的戏中感觉到,在我们进行历史战争和沉迷于身份政治的同时,我们的社区已经悄然成为了典型的亚裔澳大利亚人式社区。《海茨邻里故事》第3季是否续订且尚无定论,但如果这种强大的媒体没有带来资金和收视率,没有使该剧成为澳大利亚21世纪的电视标志而是任其默默消失, 那么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Image: an exhibit marking 50 years of television in Australia. Credit: Glenn Brown/Flickr.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on February 23,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