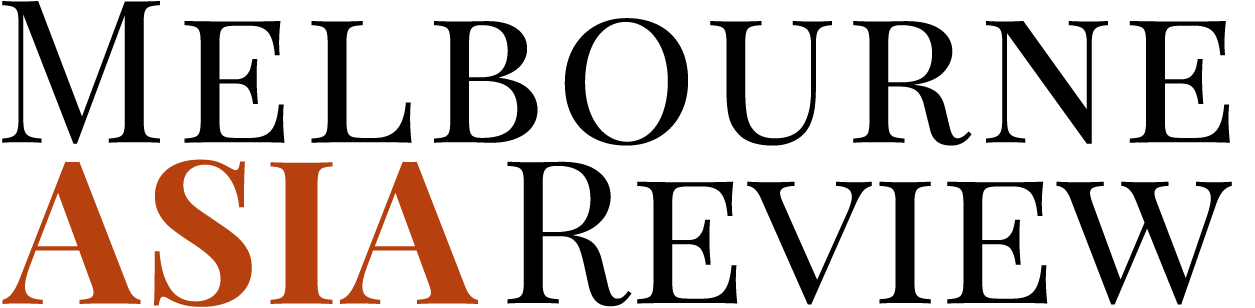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郭佩珊 俞婧雯 朱佳璇
在 1993 年的电影《侏罗纪公园》中,人们第一次见到了三角龙。虽然外表可怕,这只食草的恐龙却身患重病。令人震撼的体型和身上的盔甲掩盖了它的怯懦。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1997 , p. 284 )用它来比喻苏联:
从外表上看,这只野兽体型庞大、皮肤坚硬,武器装备齐全、姿态咄咄逼人,看起来非常可怕,没有对手敢与之纠缠。不过,表象是骗人的,因为它的消化、循环和呼吸系统正在慢慢堵塞,然后渐渐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一个三角龙吗?它的竞争对手是否恐慌于其军事外骨骼,而忘记了它可能隐藏的秘密?中国在经济上的无处不在是否掩盖了北京面临的诸多挑战?本文探讨了中国的四个潜在弱点:地理、意识形态、经济,以及外交,并提出这些弱点是否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弱点确实存在,我在下文将解释原因。
当然,中国有很多优势。我的论点并不是说中国是恐龙(不是因为自身弱点,而是最终被小行星摧毁的物种),也不是说中国是纸老虎或纸龙。苏联的解体是一个诱人的模型,尽管这个模型在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的走向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中国拥有巨大的实力和潜力,并且都有据可查。后毛泽东时代(1976 年起)中国开放全球贸易以来,中国人民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就令人瞩目。
从 60 年前的大规模人祸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混乱,再从毛主义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已重新演变为世界事务中的决定力量。如果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美国力量”,那么在 21 世纪,“中国崛起”则取而代之。如果没有中国客户,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将无法想象。西方大学的商业模式一直以满足雄心勃勃的中国中产阶级为前提。他们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疫情前每年15万名);澳大利亚人则把85%的铁矿石运往中国。
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崛起。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防开支数字不应掩盖中国政权从事胁迫性“灰色地带”活动的能力:通过操纵货币或网络间谍活动破坏政权稳定。财富和技术使中国政府能够通过提供援助、信贷和投资(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建立新的联盟。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权力投射包括动员和(或)恐吓华人华侨。中国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转型,经济也不是中国的唯一优势。
然而。
弱点依然存在
有四个方面需要确定: 地理、 意识形态、经济、外交。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方面都包括一系列因素,因篇幅有限无法在此详加分析。无论是单独考量还是综合来看,这几个方面都能指向那些对华激进派所忽略或轻视的东西。这些弱点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共产主义制度中努力创新的影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受制于规定(其往往禁止创新)。
地理限制了中国的实力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地理上的巨人,并据此推断中国注定会获得压倒性的全球力量。但将中国的地理位置与美国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另一番景象。中国不得不在一个危险的地缘环境中繁荣发展。它被重重包围。在中国的14个陆地边界周围是一些不太信任它的邻国,中国曾与之交战,且现在仍在交战。美国有南北两个邻国且都是朋友。美国的东西两侧是巨大的海洋。美国人经常利用这一平台向全球投射自己的力量。自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入侵和(或)占领了八个国家(时间长短不一,获胜程度也不尽相同)。中国自1979年(对邻国越南发动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后就再也没有在中国境外打过仗。中国的地理位置让它纠结于来自内部的威胁——藏独、疆独、港独——而非外部对手。台湾问题是对中国的冒犯,不仅是因为太晚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台湾距中国大陆160公里,位于中国竭力从对手获得安全保障的三个海域(东海、南海和菲律宾海)中间。地理位置迫使中国从地区角度考虑问题,而美国则可以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在非洲的计谋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内经济所需的化石燃料。从非洲进口碳氢化合物可以减轻(但不会消除)中国对澳大利亚等地区出口国的依赖。同样,“金砖倡议 ”是习近平对中国地理困境的回应,而非带有任何扩张野心。陆地‘带’眺望着欧亚大陆黯淡的远景——中国在那里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和印度的地缘战略挑战。被误称为“道路”的部分则是努力保持水上通道进而进入印度洋—太平洋市场,挑战美国海军的优势,但却没有能力取代它。南海只占中国疆域的一小部分,但却被习近平放在了优先位置,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在南海能比解放军在陆地上更加自由行动。在拉达克与印度的冲突就证明了中国陆地边界的不稳定。同样,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其地区野心也因这一现实而形成。
意识形态:所有共产主义都会失败
如果地理位置对中国不利,那么它所宣称的意识形态又如何呢?共产主义推动中国强大的理由很简单。1949年之前的100年里,中国从屈辱走向无政府,从被占领走向内战。毛泽东以巨大的人力代价取得的成就就是让意识形态服务于稳定的需求。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过去70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茶话会’,但他创建的政权却一直保持稳定。服从的压力很大,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党员(总数超过 9500 万)稳固了共产主义政权官僚机构的持久延续性。中国共产党注重吸纳青年入党;2018 年入党的青年中,超过 80% (164 万人)在 35 岁以下。
但作为官僚体制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否定中国权力?在审视中国意识形态的细微差别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所有其他形式的覆盖全国的应用共产主义都失败了。它们要么垮台(如苏联),要么成为一盘散沙(如朝鲜)。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繁荣(但繁荣程度却极不均衡)。在其他地方,共产主义都失败了,或者适应了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秩序(如越南),或者试图适应但最终走向失败(如戈尔巴乔夫的苏联)。1989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反应表明,该党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绝对必要性。这种对抗议和意识形态多元性的不容忍在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都很明显。接受批评和改革的共产主义政权都灭亡了。中共领导人在学习苏联解体这一“科目”时仍是“学生”。
当然,中国的共产主义(现已进入第八个十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成功得多,但这需要付出代价。这个政权依赖于强大而圆滑的领导人。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神化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决心,反而说明了不安全感。共产主义的“伟人”理论需要这样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却寥寥无几。这一历史现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信任习近平本人,并拥护他。这个政权拥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并不是因为它自信,而是正如苏尔曼·瓦西夫·汗(Sulmaan Wasif Khan)所言,因为它“被混乱所困扰”。困扰中国政府的是来自于对无法强加其统一性的领导体制的恐惧,而不是对共产主义的自豪感。毫无疑问,习近平要向下一任领导人过渡,这更有可能加深这种心理上的焦虑,而不是消除它。
同样是和中国一样进行意识形态实验,而美国却不依赖于伟大的领导人。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法律而非人类为基础的体系。美国从一创立就在地缘战略上无足轻重,到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其说是伟大的总统,不如说是平庸的总统。从亚伯拉罕·林肯(1865年)到威廉·麦金利(1897年)之间的历任总统,大多是让人遗忘的凡俗之人。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实力惊人地崛起,其规模只有现代中国可以与之媲美,这为美国在20世纪的超级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所证明的那样,美国的制度比领导它的政治家更强大、更持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至少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事实上,习近平政权结束后可能出现的责难,鉴于其内部的反腐战争,很可能会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存在构成威胁。民主党派可以在失去权力后重整旗鼓,而非共产党。
经济:规模并不代表一切
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一直被其经济成就所掩盖。可是,现在这种成功陷入停滞局面,政治和经济问题互相重叠。一个以经济成就为统治基础的政权将面临巨大的冲击。经济挑战来自两个层面:国外和国内。就国内而言,中国共产党必须安抚中国的中产阶级,否则就有可能危及自身的稳定。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与张维维的辩论中引用了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的话来提醒我们 “革命从来不是穷人创造的”:
革命实际上是由中产阶级创造的。革命是由受过教育、享有机会的人创造的。但这些机会却被政治或经济制度所阻碍。正是他们的期望值与体制能否满足他们的期望值的能力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政治动荡。因此,我认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并不能保证不发生叛乱,反而是造成叛乱的原因。(p.167)
鉴于中国起源于一场农民革命,保持资产阶级的幸福感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这意味着获得廉价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例如,中国共产党对煤炭价格上涨感到不安。它越来越依赖澳大利亚等国(该市场满足了中国 60% 的铁矿石需求)来获取对其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的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发现巨额财富并不总是等同于地区霸权,更不用说全球霸权了。大国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为世界强国。19 世纪 30 年代,中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份额与现在不相上下;中国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体,也即将成为现在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正如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所言,这并没有促使中国转化为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反,中国是外国干涉、不平等条约以及在英国人(始于19 世纪40年代)和日本人(止于20 世纪40年代)手中 “屈辱世纪”的先驱。即使在今天,正如杰夫·雷比(Geoff Raby)所记录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架构。
中国共产党需要纳税人来保持经济实力,但其却制造了自己的人口危机。如今,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比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少。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政府一直实行计划生育的一孩政策,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老年人无法享受到众多子女(和纳税子女)的扶持。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期间,活产并得以存活的孩子绝大多数是男性。据亲北京的《环球时报》报道,“男女性的比例为6:5…….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可能需要几十年才得以解决”。男性不仅需要经济机会也需要伴侣。
中国能租到朋友,但买不到朋友
中国国家内部与外部的挑战交织在一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为中国的财富和权力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其内部矛盾,以及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于这些矛盾的狂热利用。中国玩了一场更为复杂的外交游戏,利用美国的力量和西方的希望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其结果是,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贫穷流氓国家,转变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数百万人带来繁荣的引擎。这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之一,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也有局限性,并引起了一些对抗性的回应。
由于其巨大的财富,中国的外交仍然是高度交易性的。从所罗门群岛到俄罗斯,他们与中国结盟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文明或意识形态。日本和韩国尽管与中国共享儒家文化,但仍是中国实现地区抱负的主要障碍。中国的正式盟友很少,而美国的则很多。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没有与五眼联盟、四方联盟或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相当的组织。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和发展将受到无休止的争论,但正如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的那样,这增加了外国对中国实力的不信任,使建立联盟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也明白这一点。中国对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堪培拉、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一项潜艇协议)的愤怒,不仅是因为其认识到中国缺乏与之类似的长期盟友,也是出于其对中国水域构成军事威胁的考虑。中国缺乏美国现在几乎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深厚的同盟关系。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詹宁斯(Peter Jennings)说,中国知道自己很难在除一党制国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交朋友。
俄罗斯有时被认为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但即使如此,我们也看到指导原则是交易主义,而不是价值观或理念,除了粗糙的反美主义。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Christensen)认为,“中俄关系没有达到真正的联盟水平”:
很难想象中国会直接介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斗争,或者未来在波罗的海的冲突。同样,很难想象俄罗斯军队会直接介入台湾海峡冲突或其他东亚海上争端。事实上,俄罗斯向越南和印度出售先进的武器系统,而越南和印度是中国主权冲突中的对手。
“一带一路”倡议被标榜为地区繁荣的建设者,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威尔·赫顿(Will Hutton)可能夸大了他的观点,但他抓住了对“一带一路”倡议更为普遍的评价,认为这是“21世纪中国通过债务进行的公开准殖民。70个签约国基本上同意向中国的外交政策卑躬屈膝,以换取中国建设基础设施的软贷款。”
西方殖民主义很难说是对外交政策成功的研究。但是,尽管(有时正是因为)这段历史,西方的结盟仍然很坚固。正如奥莉安娜·斯凯拉·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所言:
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中有八个是民主国家,且中国近 60% 的出口流向美国及其盟国。如果这些国家以断绝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来应对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其经济代价可能会威胁到习近平复兴计划中的发展部分。
自1989年以来,美国所打的战争都有盟友支持。例如,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参与美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甚至包括越南战争。除了朝鲜,中国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 “忠诚储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涉及对外战争时的谨慎:中国没有天然盟友来对抗它们。
这种结盟能力上的不平衡应是地区和平的好兆头。问题在于中国对美国决心的看法。可以想象,习近平对台湾的图谋,正如他对香港的打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预期到美国总统不会组织去应对这些图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和北约目前不愿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态度,证实了一种衰落主义的论调,即中共冀盼进步。美国的弱点是中国纠正自身长期外交弱点的基础。如果习近平判断失误,如果他将阿富汗和乌克兰视为加强其好战心的理由,像普京在基辅未能做到的那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台北,那么冲突的潜在风险就会增加。
结论
关于中国力量的概念有一个悖论:如果中国的弱点使其更有可能扰乱地区秩序,西方及其盟友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加固中国的优势,以维护地区秩序?如果中国共产党是偏执狂,并由此产生误判,那么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难道不应该试图处理而不是令局面恶化吗?当然,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的邻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尝试处理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基于历史的假设,认为随着中国的繁荣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将在政治上实现自由。从尼克松总统到奥巴马的总统,他们对这一预言充满信心,却忽视了这一预言导致的美国去工业化。但 “他们和我们一样” 的论调经久耐用,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如本文所述,如果中国在其位置上的弱点趋向于大多数政体希望避免的地区不稳定,那么美国的战略必须通过遏制来继续平衡与中国的接触。这种弱化劣势与否定优势的协调需要良好的外交技巧,以及明智地使用诱导和威胁手段。然而,这些都无法保证奏效。大国政治无法提供多重保证。但是,对中国的弱点保持敏感,而不是对其优势感到烦恼,将有助于对地区秩序的走向做出更有力、更现实的评估。
Image: Beijing Military Museum. Credit: pwyliu/Flickr.
English version here.